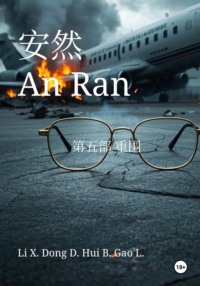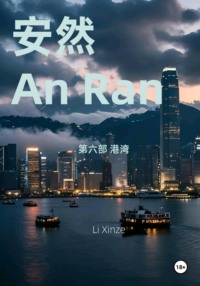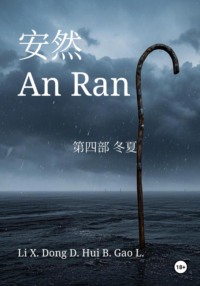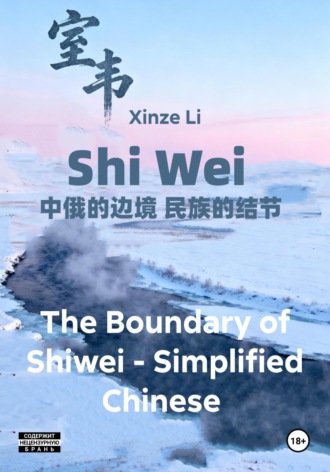
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
The Boundary of Shiwei – Simplified Chinese
张军停下脚步,站在离她十步远的地方。这十步的距离,像一道鸿沟,一边是他充满“贪婪褶皱”的过去:在北京的办公室里,为了流量写耸动的标题,为了合作迎合别人,为了数据熬夜到凌晨;一边是她所代表的“历史色彩与身份认同”:从圣彼得堡来,修复百年壁画,寻找自己的根,手里的笔在填补历史的裂缝,也在填补自己的内心。
他的心跳得很快,手心有点出汗。胖胖的圆脸上,汗毛在冷冽的空气里收缩,有点痒。他开始自我对话,像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精神博弈。
“上去吧,张军。”一个声音说,“你来到室韦,就是为了寻找一个锚点,寻找和自己一样的人。她就是那个锚点,她懂你的挣扎,懂你的渴望。”
“别去。”另一个声音立刻反驳,“你配吗?你的手上沾满了流量和算法的脏东西,你以前拍照片是为了变现,现在看到她,是不是又想拍一张‘纯净的修复师’的照片,来满足自己的虚伪?你只是想利用她,来证明自己‘洗心革面’了,其实你还是以前那个贪婪的人。”
罪恶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,淹没了他,刻在他的灵魂上,现在被教堂的寒意一激,又开始疼。
他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,她填色的动作很轻,很稳,像在呵护一件易碎的珍宝。他想起自己拍过的那些视频,像一堆廉价的塑料花,没有生命,却占满了他的生活。“我真的能变好吗?”他问自己,声音很轻,在教堂里回荡。
女人突然停下了手里的笔,转过身。她的目光和张军的目光撞在一起,没有惊讶,没有警惕,只有一种清澈的、直率的好奇–像艺术家看一件陌生的作品,想知道它的故事。
“你是那个新来的摄影师?”她开口,声音有点低,带着中国东北口音特有的醇厚,却又夹杂着一丝轻微的俄语颤音,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流,带着一点异域的涟漪。这种文化交融的细微之处,在室韦随处可见,却在她的声音里,显得格外动人。
张军的喉咙有点干,他咽了口唾沫,往前走了两步,又停下–还是没敢走完那十步。他没有像以前那样,脱口而出“我是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”,也没有说“我以前是央视记者”,他选择了自己在室韦的新身份,一个他正在慢慢适应、也慢慢喜欢的身份:“是的。张军。我只是一个,沉默寡言的摄影师。”
他刻意强调“沉默寡言”,像是在和过去那个喋喋不休、为了流量说尽废话的自己划清界限。
女人笑了,嘴角弯起一个浅淡的弧度,眼底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–像是长时间盯着壁画,眼睛累了,也像是长时间寻找,心里累了。“娜斯佳。”她报出自己的名字,指了指墙上的壁画,“我是来修复这里的。修复那些快要消失的颜色。”
她的手指落在壁画上圣徒的衣角处,那里的蓝色已经褪成了浅灰,裂缝里积着灰尘。“这些颜色里藏着过去的故事,是中俄混血后裔的故事,也是我的故事。我想把它们修回来,看看能不能找到我自己的位置。”
张军的心猛地一跳。“找到自己的位置”–这句话,正是他来到室韦的原因。他看着娜斯佳的眼睛,那里面有和他一样的迷茫,也有和他一样的渴望。他突然觉得,那十步的距离,好像没那么宽了。
他深吸一口气,教堂里的寒意顺着鼻腔钻进肺里,却让他觉得清醒。他想起额尔古纳河上空永恒的静谧,想起小木屋里温暖的壁炉,想起瓦西里的马和王光的列巴。他知道,自己的隐居生活,不是结束,而是刚刚开始;他的灵魂试炼,不是独自承受,而是有了一个可能同行的人。
“那些颜色,很难修吧?”他问,声音比刚才稳了一点。
娜斯佳点点头,又拿起笔,对着壁画:“很难。得先分析原来的颜料成分,再找一样的颜色,一点一点填,不能急。就像找自己的根,也不能急,得慢慢等,慢慢看。”
张军看着她低头填色的样子,阳光落在她的笔上,笔尖的颜料闪着微光。他拿出相机,没有对准她,而是对准了壁画上那处刚被填上一点蓝色的衣角。他按下快门,“咔嚓”一声,很轻,却像一颗种子,落在了他的心里。
他留在了室韦。不是因为逃避,是因为这里有他要找的根,有他要修的灵魂,还有一个和他一样,在寻找颜色与身份的人。额尔古纳河的水还在流,白桦林的风还在吹,他的相机里,会慢慢装满室韦的晨昏,装满真实的生活,装满一个灵魂从迷茫到清醒的,所有痕迹。
教堂里的寒意还裹着松木与苔藓的沉味,张军的声音落在斑驳的壁画前,带着一种被岁月磨过的厚重–那是十年莫斯科记者生涯养出的敏锐,也是两年流量漩涡里熬出的疲惫。他盯着娜斯佳指尖下那块褪色的群青,像盯着自己心里某个模糊的角落,“你修复的是色彩,还是信仰?”
娜斯佳的手指顿了顿,没有立刻回答。她的指甲缝里嵌着深浅不一的颜料,深蓝、赭石、金粉,像把壁画的历史都藏进了指缝。她轻轻抚摸着墙壁,指尖划过那些细碎的裂纹,像是在触摸一群沉睡的故事。“你觉得信仰是什么?”她转过身,浅棕色的眼睛在昏暗里亮着,像额尔古纳河面上的星。
娜斯佳放下手里的细毛笔,笔杆上还沾着一点未干的群青。她靠在小木屋的墙壁上,后背抵着微凉的原木,叹了口气。“我修复的是历史的色彩。”她的目光又落回壁画上,落在那个半边脸已经模糊的天使身上,“你看,这些颜料里藏着的不只是颜色,是故事。沙俄贵族逃亡的时候,带着东正教的画师来这里,画师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颜料,用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粉,才画出了这些天使和圣徒。”
她指着天使的眼睛,那里的颜料已经褪成了浅灰,只剩下一点微弱的蓝影。“这个天使,它不是完美的。你看它的眉骨,是皱着的;它的嘴角,是往下垂的–它带着痛苦。以前我在圣彼得堡的冬宫看壁画,那些天使都是笑着的,金光闪闪的,可这里的不一样。后来我才明白,痛苦才是信仰的基石。”
张军往前走了两步,离壁画更近了。他的目光落在天使的眼睛上,那点模糊的蓝影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他自己。在北京的时候,他也有过“痛苦”,可那是工作的痛苦,是焦虑,是挣扎,是纠结。那些痛苦像潮水,把他裹在里面,可他从来没想过“扛过去”,只想着“逃开”。
“痛苦?”他低声重复,声音里带着自嘲,“我在城市里经历的痛苦,算什么痛苦?是早上醒来,打开手机看到播放量掉了两千的恐慌;是写文案时,在‘真实’和‘虚假’之间反复横跳的恶心;是晚上躺在床上,想起自己今天又说了谎,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愧疚。每天早上,我的内心都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试炼:我是要做回那个拿着相机去追真相的记者,还是继续屈从于数据,做一个哗众取宠的数据奴隶?”
“所以你逃到了室韦。”娜斯佳的语气很平淡,没有指责,也没有同情,却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,剖开了他的伪装。她的目光落在他的圆脸上,落在他因为常年过度进食而微微下垂的嘴角,好像能看穿他藏在脂肪下面的挣扎。
张军的脸有点发烫,不是羞愧,是一种被理解的局促。“我不是逃。”他辩解,声音却比刚才轻了些,“我是来寻找一种救赎的契机。信仰的剥落,会导致道德的崩溃,你知道吗?当一个人发现,用谎言和煽动性情绪就能轻易获取财富和名声时,他内心的善恶会被推到什么极致的边缘?”
他想起自己最出名的时候,有个品牌找他合作,让他推荐一款“能预防新冠”的保健品。他查了资料,知道那是虚假宣传,可品牌给的钱是他三个月的收入。他犹豫了三天,最后还是拍了视频,对着镜头说“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吃,效果很好”。视频发出去后,他收到了很多私信,有人问他在哪里买,有人说“谢谢张军同志推荐”。他看着那些私信,心里像被灌了铅,沉得喘不过气。后来,那款保健品被曝光是假货,他删了视频,却再也没敢看那些私信。
娜斯佳没有回答,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她的眼神很软,带着一种悲悯的基调,不是可怜,是理解–她好像在说,你所经历的这些挣扎,不是你一个人的,是我们这代人的困境。在圣彼得堡的时候,她也遇到过类似的事:画廊让她修改一幅油画,把“流亡贵族的痛苦”改成“异国风情的浪漫”,说这样能卖更高的价钱。她拒绝了,然后失去了那份工作。
“你呢?”张军突然反问,把话题从自己身上移开。“你为什么离开圣彼得堡,来到这个边境小镇,修复一座几乎被遗忘的教堂?是为了追逐那份历史印记?还是为了追逐你那中俄混血的身份认同?”
娜斯佳沉默了。她低下头,手指在颜料盒上轻轻摩挲,像是在整理混乱的思绪。这个动作很轻,却带着一种刻意的迟缓–像是在掩饰心里那些不愿意轻易说出口的真实想法。教堂里很静,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风声,和远处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。
过了一会儿,她才抬起头,目光落在壁画的一个角落里,那里有一块几乎完全褪色的蓝色,只剩下一点微弱的痕迹。“色彩会说谎,张军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落在雪上的羽毛,“历史也会。我祖父是沙俄贵族的后代,他告诉我,他们当年离开俄罗斯,是‘光荣的流亡’–为了守护东正教的信仰,为了不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妥协。我从小就听着这个故事长大,家里的相册里,有祖父穿着军装的照片,有祖母戴着珍珠项链的照片,他们的眼神里,全是骄傲。”
她顿了顿。“去年,我外婆去世前,给了我一封信,里面有全部的真相。我的曾祖母就是跟着祖父一起来中国的,他们当年离开,不是什么‘光荣的流亡’,是因为害怕布尔什维克,他们一路乞讨才到了室韦。后来,我来了这里,来寻找他们当年生活过的痕迹。”
娜斯佳的声音有点发颤,她拿起一支细笔,蘸了一点天青石粉调成的颜料,却没有往壁画上涂,只是让笔尖悬在半空。“我来这里,不是为了追逐历史,也不是为了寻找身份。我是想在这些壁画里,找到一个真实的坐标。像这幅壁画上的颜色,有剥落的,有残留的,有后来补的。我修复它们,不是在还原历史,是在寻找一个可以放置我灵魂的地方–我到底是谁?是圣彼得堡的贵族后代,还是室韦边境小镇出生的混血儿?”
她指着壁画上那块褪色的蓝色:“你看这片蓝色,它不是普通的颜料,是用室韦附近山上的天青石磨成的粉,用额尔古纳河的水调成的。只有用这片土地上的材料,才能让这幅画真正地活过来,才能和墙壁融为一体。我的身份,就像这片壁画,需要用室韦的泥土、河水、松木来重新固定–我需要知道,我有自己的家乡,自己的家族,自己的故事。”
张军看着她,突然明白了。他们其实是一样的人。他拿着相机,在室韦的晨雾里拍鸟叫,拍驯鹿,拍小木屋的炊烟,不是为了做博主,是为了在镜头里找到自己–找到那个曾经为了真相而奔跑的记者;她拿着画笔,在教堂的昏暗里填颜料,修壁画,不是为了做修复师,是为了在色彩里找到自己–找到那个不被虚假历史绑架的娜斯佳。
他们的工具不同,一个是相机,一个是画笔;他们的方式不同,一个是记录,一个是修复;但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–在宏大的绝望里,找到个体存在的意义。算法的绝望,历史的绝望,身份的绝望,这些绝望像一张网,把他们裹在里面,可他们都在挣扎,都在寻找一个破网而出的出口。
“天色晚了,去我住的地方吧。”娜斯佳收起颜料盒,把毛笔放进笔袋里,“离这里不远,也是一间小木屋,有壁炉,能暖和点。”
张军点点头,跟着她走出教堂。外面的天已经黑了,室韦的夜晚没有路灯,只有家家户户窗户里透出的暖黄灯光,像撒在黑夜里的星星。风比白天更冷了,刮在脸上,带着一点雪粒子的凉意–室韦的冬天快到了。
娜斯佳住的小木屋在教堂旁边的一条小巷里,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俄式煤油灯,煤油灯里的蜡烛在风里轻轻晃,映得门口的积雪泛着暖光。娜斯佳推开木门,一股干燥的松木香气立刻涌了出来,混着壁炉里松木燃烧后的焦香,一下子把外面的寒意挡在了门外。
“进来吧,我刚生了火。”娜斯佳脱下外套,挂在门口的木钩上,外套上沾着一点雪粒子,很快就化了。
张军走进屋里,脱下帽子,露出有点汗湿的头发。屋里很暖和,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旺,火焰跳动着,发出“噼啪”的响声,把橘红色的光投在墙上,墙上挂着几幅娜斯佳画的素描:有额尔古纳河的晨雾,有白桦林的霜花,还有这间教堂的遗址。
“我喜欢这里的干燥。”张军看着壁炉里的火焰,心里的紧绷慢慢放松下来,“没有被城市里面工业的气味–北京的空气里,全是汽车尾气、香水、外卖的味道,混在一起,让人喘不过气;南方古镇的空气是湿的,霉味能钻进骨头里。只有这里的空气,是干净的,是松木的味道,是雪的味道,是河水的味道。”
娜斯佳笑了笑,转身走进厨房。厨房很小,也是原木做的,灶台上放着一个铁锅,锅里炖着红菜汤,香气从锅里飘出来,带着甜菜的甜和牛肉的香。“等一下,晚餐马上好。”
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,看着火焰。火焰的影子在墙上晃,像跳舞的精灵。他想起自己租的那间小木屋,壁炉里的火也是这样,晚上他会坐在壁炉旁,整理白天拍的照片,写一点笔记。有时候,他会对着壁炉发呆,听着松木燃烧的声音,心里很静–那种静,是在北京从来没有过的。
很快,娜斯佳端着晚餐走了出来。一盘切得厚厚的列巴,面包皮是金黄色的,还冒着一点热气;一小碗蓝莓酱,是深紫色的,里面能看到整颗的蓝莓;还有一碗红菜汤,汤是深红色的,上面浮着一点酸奶油,像雪落在红地上。
“没有伏特加和腌黄瓜吗?”张军笑着问,他想起了瓦西里–第一次在河边见到瓦西里的时候,瓦西里就给了他一根腌黄瓜,说“喝伏特加就得配这个”。这几天,他们一起在河边喝过一次伏特加,瓦西里的伏特加是自己酿的,很烈,喝下去像火烧,配着腌黄瓜,却格外爽口。
娜斯佳也笑了,把列巴推到他面前:“明天吧,今晚,我们只吃最普通的食物。”
张军拿起一块列巴,咬了一口。面包皮很脆,“咔嚓”一声,里面的面包很软,带着浓郁的麦香,还有几颗细小的燕麦粒,嚼起来有嚼劲。他蘸了一点蓝莓酱,蓝莓的酸甜和麦香混在一起,味道很纯粹–没有添加剂的甜,没有防腐剂的涩,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。
“这才是纯净的生活。”他一边咀嚼,一边说。这种感官记忆突然和他小时候的记忆重叠了–张军的奶奶也经常烤这样的列巴,早上的时候,奶奶会把列巴切成片,抹上一点黄油,或者蘸着自制的果酱,他会捧着列巴,坐在窗边,看着外面的雪。那时候的生活很简单,没有数据,没有流量,只有奶奶的笑容和列巴的香味。
娜斯佳也拿起一块列巴,慢慢吃着。“我刚来室韦的时候,每天都在教堂里待着,对着那些褪色的颜料,感觉自己越来越与外界隔离。”她的声音很轻,像在自言自语,“有时候,我会一整天不说一句话,就坐在那里,看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,落在壁画上,看着那些颜色在光里慢慢变亮。”
“我以前在圣彼得堡读大学的时候,那里每天都很热闹。画廊的展览,朋友的聚会,还有各种采访–大家都叫我‘年轻的油画天才’,可我一点都不开心。我总觉得,那些画不是我的,那些赞美也不是给我的。”她喝了一口红菜汤,汤很烫,她轻轻吹了吹,“然后我来到这里,没有展览,没有采访,没有赞美,可我觉得踏实。每天修一点壁画,晚上回来烤列巴,喝红菜汤,心里很静。”娜斯佳说。
张军点点头,他懂这种感觉。在北京的时候,他每天都很“忙”:赶文案,拍视频,开直播,见合作方–手机响个不停,微信消息一条接一条,可他总觉得,自己像一个陀螺,被别人抽着转,停不下来。来到室韦,他每天只做几件事:早上去河边听鸟叫,上午跟着瓦西里去林子转,下午整理照片,晚上坐在壁炉旁写笔记–很闲,可他觉得很充实。
“我现在能精准识别二十种鸟类的叫声了。”张军说,语气里带着一点骄傲,“柳莺的叫声是‘叽叽啾啾’的,很细;树莺的叫声带‘咕噜’的尾音;啄木鸟敲树干的声音是‘笃笃笃’的,很有节奏。”
他想起昨天早上,他在河边听到一种从来没听过的鸟叫,“啾–啾–”的,很长,很亮。他站在那里,听了很久,后来瓦西里告诉他,那是北红尾鸲的叫声,只有秋天的时候才会来这里。“以前在城市里,我连麻雀和鸽子都分不清楚,每天听的都是手机提示音,‘您的视频有新评论’‘某某品牌邀请您合作’–那些声音像噪音,吵得我心里发慌。”
娜斯佳放下勺子,看着他,眼神里带着一丝认同。“当你的感官被净化时,你才能听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喧嚣。”她低语道,“在圣彼得堡的时候,我每天都被各种声音包围:汽车的鸣笛声,画廊的音乐声,朋友的说话声–我听不见自己心里的声音。来到这里,没有那些噪音,我才能听见自己在想什么,才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”
她指着壁炉里的一块松木,松木正在燃烧,发出“噼啪”的响声,火星偶尔会跳出来,落在壁炉的石头上,很快就灭了。“你看这块木头,它在燃烧的时候,会发出声音,会发光,会发热–这是它最真实的样子。我们也是一样,只有去掉那些外在的东西,去掉‘博主’‘修复师’‘贵族后代’这些标签,才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。”
张军看着那块燃烧的松木,心里突然很通透。他想起自己注销账号的那天,看着“账号已注销”的提示,心里空落落的,可也有一种解脱。他终于不用再为了“国际知名博主”这个标签而活,不用再为了流量而妥协。他只是张军,一个喜欢拍照,喜欢听鸟叫,喜欢吃列巴的人。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看着娜斯佳,眼神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,“我们都在寻找真实的自己,只是用的方式不一样。你用画笔,我用相机;你在色彩里找,我在镜头里找。”
娜斯佳笑了,这次的笑容很轻,却很真实,没有了之前的疲惫。“或许,我们可以一起找真实的自己。”
壁炉里的火焰还在燃烧,橘红色的光映在他们的脸上,很暖。窗外的风还在刮,可屋里很静,只有松木燃烧的“噼啪”声,和红菜汤的香气。张军拿起一块列巴,又蘸了一点蓝莓酱,慢慢吃着。他知道,这个夜晚,只是他在室韦的普通一晚,也是他灵魂救赎的开始。而娜斯佳的出现,像一束光,照亮了他之前迷茫的路–或许他们会一起,在颜料与镜头的世界里,找到那个真实的自己,找到生存的意义。
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,从窗外传来,很轻,却很坚定,像在为他们的约定伴奏。室韦的冬天快到了,雪会覆盖大地,会覆盖白桦林,会覆盖教堂的遗址,可壁炉里的火会一直烧着,列巴的香气会一直飘着,他们的对话,也会一直继续着–关于信仰,关于道德,关于生存的意义,关于那个真实的自己。
夜深得像额尔古纳河的底,浓稠得化不开。窗外的寒风突然变了性子,不再是傍晚时那种带着雪粒子的轻拂,而是裹着蛮力,呼啸着撞在小木屋的原木墙上,发出“呜呜”的响,像远处驯鹿群的哀鸣,又像那些被历史埋在河底的故事,在黑夜里拼命想探出头来。
小木屋里的火光却很稳。壁炉里的松木烧得正酣,橘红色的火焰舔着原木,每烧到纹理粗糙的地方,就“噼啪”响一声,溅起几点细碎的火星,落在冰冷的石头上,瞬间灭了,只留下一点焦黑的印子。张军坐在壁炉旁的木椅上,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红菜汤,汤碗的热度透过瓷壁传到掌心,暖得他指尖发麻。
他看着娜斯佳。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,手里摩挲着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–蛋壳是淡绿色的,上面用金色的颜料画着缠枝花纹,只是花纹已经磨损了大半,露出底下苍白的蛋壳,像一件被时光啃过的旧物。她的侧脸在火光里半明半暗,高挺的鼻梁投下一道浅影,落在沾着颜料的工装袖口上,看起来既脆弱又坚韧。
“我们都没什么可瞒的了。”张军突然开口,声音很低,被壁炉的“噼啪”声衬着,显得格外沉,像从喉咙深处滚出来的石头,“这屋子太小了,风又太吵,藏不住心事。”
娜斯佳抬起头,浅棕色的眼睛在火光里亮了亮,她放下彩蛋,点了点头:“嗯,藏不住。”
张军深吸一口气,把手里的红菜汤放在桌上。汤还冒着热气,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缕白汽,很快又散了。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木椅的扶手–那扶手被人摸了多年,已经磨得光滑,带着人的温度。
“我辞职,不是因为厌倦了工作,是因为我厌倦了自己。”他说,每一个字都咬得很实,“从央视辞职,从莫斯科回来,我以为我能做自己想做的报道,能守住以前的日子。可我错了,我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。”
他的思绪飘回了莫斯科。二十多年前,他刚到莫斯科当记者,他第一次去采访一个莫斯科的老工匠。老工匠在莫斯科郊外的小作坊里,做了一辈子的套娃,他的套娃不涂鲜艳的颜色,只用水彩轻轻晕染,画的都是莫斯科的老街道、老房子。张军在作坊里蹲了一周,每天跟着老工匠一起起床,一起煮茶,一起削木头。老工匠告诉她:“套娃的灵魂在木头里,你得听木头的话,它想变成什么样,你就把它刻成什么样,不能勉强。”
那篇报道发出去后,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,是一个老人写的。老人说,他年轻时在莫斯科待过,看了张军的报道,想起了当年在莫斯科街头吃列巴的日子,“谢谢你,让我又回了一趟莫斯科”。那时候,张军觉得自己手里的笔有分量,相机有温度–他记录的不是新闻,是人的故事,是能让人心里发暖的东西。
“在莫斯科的十几年,是我最纯粹的日子。”张军的声音软了些,带着一点怀念,“我坚信深度报道的意义,坚信镜头能留住真实。那时候,我跑遍了俄罗斯的大小城市,从圣彼得堡的冬宫到贝加尔湖的奥利洪岛,从摩尔曼斯克的极光到索契的黑海。我见过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里,守着灯塔的老人;见过在战火里,抱着书本不肯离开图书馆的孩子;见过在草原上,跟着驯鹿群迁徙的涅涅茨人。”
他想起有一次,为了报道涅涅茨人的迁徙,他跟着他们在草原上走了半个月。每天住在帐篷里,喝着驯鹿奶,吃着冻硬的列巴。晚上,草原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,他冻得睡不着,就和涅涅茨的老人一起坐在篝火旁,听老人讲驯鹿的故事。老人说:“驯鹿是我们的家人,我们跟着它们走,它们带着我们找吃的,我们不能丢下它们。”那时候,他觉得苦,却很踏实–他知道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。
“但回到中国,一切都变了。”张军的声音又沉了下去,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,“流量成了新的权力。我写的深度报道,没人看;我拍的真实故事,播放量只有几千。可那些标题耸动、内容肤浅的抖音的视频,却能轻易破百万。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人的注意力这么廉价,原来真实这么不值钱。”
“我看到了人性的弱点–大家喜欢看漂亮的、刺激的、不用动脑子的东西。”张军自嘲地笑了笑,手指在桌上轻轻敲着,“可更可怕的是,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。我明明知道那些哗众取宠的抖音视频没意义,却还是忍不住,开始转变的我拍摄方法。我开始天天盯着后台的数据,我看着播放量一点点涨,心里竟然有点窃喜。”
“我越迎合那些廉价的情绪,我的观众就越兴奋。”张军的声音里带着悔恨,“我的账号越来越‘红火’,广告接到手软,有人叫我‘国际知名博主’,有人请我去做讲座,可我心里却越来越空。每天晚上,我都要吃很多东西才能睡着–糖醋里脊、油焖大虾、红烧肉,我把肚子填得满满的,好像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空也填上。”
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,圆圆的,像揣了个小皮球。“我胖了,娜斯佳,你知道为什么吗?”他看着娜斯佳,眼神里带着一种悲悯,不是对别人,是对自己,“因为过度进食是我掩盖空虚的唯一方式。我的圆脸、我的体重,都是我贪婪的褶皱–我贪婪名声,贪婪别人的关注,贪婪那些虚假的赞美。我嫉妒那些比我更红的年轻人,他们能轻易写出更耸动的文案,剪出更刺激的视频,我就跟着学,跟着模仿,最后把自己都弄丢了。”
他想起有一次,他去参加一个自媒体峰会,台上的年轻人分享“涨粉秘籍”,说“要抓住用户的痛点,要制造焦虑,要让他们觉得不看你的内容就会落后”。他坐在台下,手里拿着笔,却一个字也没记–他突然觉得很恶心,不是身体上的,是心里的。他看着台上唾沫横飞的年轻人,又看着台下认真记笔记的同行,觉得自己像在一个巨大的骗局里,所有人都在骗别人,也在骗自己。
“我以为屈从欲望能获得解脱,可我只得到了更深的罪恶感。”张军的声音有点发颤,他拿起桌上的列巴,掰了一块,却没吃,又放了回去,“有一次,我侄女问我:‘爸爸,你做的视频是真的吗?’我看着她的眼睛,竟然说不出话。我侄女才八岁,她都知道要讲真话,可我一个四十岁的人,却在靠说谎赚钱。”
那之后,张军开始失眠。每天晚上,他都要在客厅里待到凌晨,对着电脑屏幕发呆。屏幕上是他当天发的视频,播放量很高,留言很多,可他觉得那些数字像一个个嘲讽的眼睛,盯着他,说“你是个骗子,你是个伪君子”。他会打开冰箱,把里面的食物都拿出来,拼命往嘴里塞,吃到胃里胀得难受,吐了,再接着吃–他想用身体的痛苦,掩盖心里的痛苦。
“最可怕的是,我发现自己上瘾了。”张军的声音里满是绝望,“我表面上在做深度思辨,写关于信仰、道德、生存意义的文章,拍关于‘纯净生活’的视频,可我内心深处,只是一个渴望被虚荣心喂养的瘾君子。我用良知做包装,里面装的全是隐秘的欲望–我想红,想被关注,想证明自己有价值。”
他想起注销账号的那天。那天早上,他又失眠了,坐在电脑前,看着自己前一天发的视频–标题是“俄乌边境历史溯源: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”,内容是他花了一周时间查资料写的,可播放量只有五千。他看着屏幕上的数字,突然觉得很累,累得不想再争了。他点了“注销账号”,看着提示弹出“确认要注销吗?注销后所有数据将无法恢复”,他没有犹豫,点了“确认”。
“我来室韦,不是为了拍照片,是为了逃。”张军看着娜斯佳,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躲闪,全是赤裸的坦诚,“我想找一个网络影响力微弱、环境原始的地方,做一个彻底的隔离。我怕再待在北京,我会彻底堕落–我会为了钱,拍更虚假的视频;为了流量,说更恶毒的话。我需要这里的宁静,需要这里的寒风,需要这里的河水,来对抗我心里的非理性冲动,来把我从数据的泥潭里拉出来。”
他的话像一块石头,落在小木屋的寂静里,激起一圈圈涟漪。壁炉的火光跳了跳,映在娜斯佳的脸上,她的眼睛里没有惊讶,只有一种深深的理解–好像张军说的,也是她心里的话。
娜斯佳沉默了很久,才慢慢开口。她的声音很轻,不像张军那样充满戏剧化的挣扎,却带着一种沉默的厚重,像额尔古纳河的水,缓慢却有力量。“我的痛苦,和你不一样,张军。它是沉默的,像埋在地下的树根,看不见,却一直缠着我。”
她拿起那个巴斯克节的彩蛋,指尖轻轻划过磨损的花纹。“这是我外祖母教我做的。她说,我们是沙俄贵族的后裔,是彼得大帝时期一个将军的后代。十月革命的时候,我们的祖先带着家人和财宝,逃到了中国,来到了室韦。外祖母说,我们是‘带着文明种子来到蛮荒之地的人’,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,不能丢了贵族的体面。”
她的外祖母是圣彼得堡人,年轻时跟着家人逃到室韦,嫁给了一个中国商人。外祖母一辈子都活在“贵族”的梦里:她坚持说俄语,穿俄式的连衣裙,用银质的餐具,每天都要花一个小时整理头发。她给娜斯佳讲圣彼得堡的冬宫,讲涅瓦河的夏天,讲贵族的舞会,却很少提在室韦的日子–好像这里的生活是对“贵族身份”的玷污。
“我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。”娜斯佳的声音软了些,带着一点孩子气的向往,“我以为我们真的是贵族,以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。我在圣彼得堡学油画的时候,总是告诉同学,我的祖先是沙俄将军,我想让他们觉得我很特别。”
可去年,她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发现一封曾祖母写的信,还有几张老照片。曾祖母在信里说,贵族的身份根本不重要,十月革命的时候,他们一路乞讨到了中国,饿了就吃树皮,冷了就躲在山洞里,最后才流落到室韦。曾祖母说:“贵族的事情已经是过去式了,我们就是普通人,能活着就不错了。”
Конец ознакомительного фрагмента.
Текст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 ООО «Литрес».
Прочитайте эту книгу целиком, купив полную легальную версию на Литрес.
Безопасно оплатить книгу можно банковской картой Visa, MasterCard, Maestro, со счета мобильного телефона, с платежного терминала, в салоне МТС или Связной, через PayPal, WebMoney, Яндекс.Деньги, QIWI Кошелек, бонусными картами или другим удобным Вам способом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