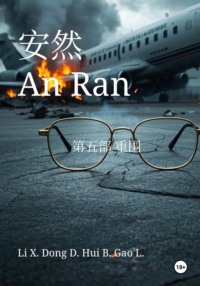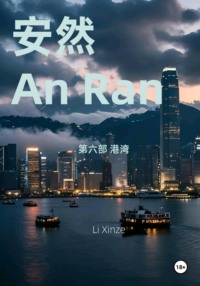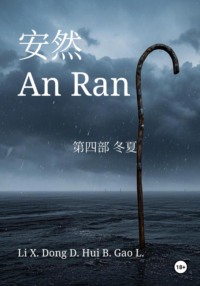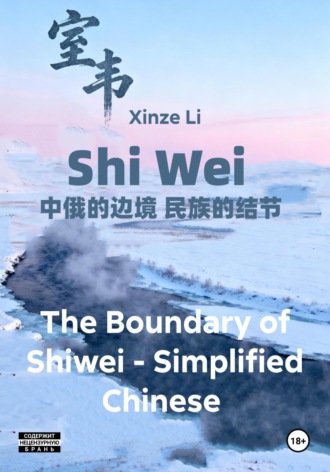
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
The Boundary of Shiwei – Simplified Chinese

Xinze Li
The Boundary of Shiwei – Simplified Chinese
1.探索
张军坐在北京老旧公寓的落地窗前,指尖还沾着半块糖油饼的油星子。那糖油饼是楼下早点铺买的,外皮炸得酥脆,咬下去能听见“咔嚓”一声,内里却软乎乎的,裹着一层厚厚的白糖,甜得能糊住舌尖。他已经吃了两个,胃里沉甸甸的,像揣了块浸了油的海绵,但他的手还是不自觉地伸向了桌上的油纸袋–那里还有最后一个。
张军,四十二岁的年纪,体重早就过了标准线。圆脸,双下巴,肚子挺得像揣了个小皮球,走路时身上的肉会跟着轻轻晃动。熟人见了他,总打趣说“张军同志发福了”,他只能笑着应和,心里却清楚,这不是简单的发福,是过度进食喂出来的空洞。就像现在,窗外的都市街巷被灰蒙蒙的雾霾罩着,高楼挤着高楼,电线在天空中织成密不透风的网,连阳光都得费劲儿才能从缝隙里漏下几缕,落在楼下斑驳的墙面上,又很快被阴影吞噬。这种窒息感,他太熟悉了–就像他每次把食物塞满嘴巴时,喉咙口那种又满足又压抑的感觉,像一块湿抹布堵在那儿,吐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。
他是“国际知名自媒体博主”,这头衔是他辞职后自己给的,后来被一些媒体引用,慢慢就传开了。每次介绍自己时,他都能感觉到这几个字里的虚浮–“国际知名”,到底多知名?是在海外社交平台有几百万粉丝,还是能接到几个跨国品牌的广告?其实都没有。所谓的“知名”,不过是他在央视做驻莫斯科记者时攒下的一点老本,是那些年跑遍俄罗斯大小城市写下的报道,是镜头里定格的克里姆林宫的雪、贝加尔湖的蓝、圣彼得堡冬宫的金色穹顶。可现在,那些都成了“过去式”。
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,手腕上还戴着当年在莫斯科买的那块机械表,表盘已经有些磨损,指针在“10:17”的位置轻轻跳动。十年前,他就是戴着这块表,拎着行李箱从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,回到了北京。那时候,他刚从中国央视辞职,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–他想做更自由的新闻报道,想把那些在央视没能说透的故事,用自己的方式讲给更多人听。可十年过去,他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:每天盯着自媒体视频网站后台的流量数据,为了一个耸动的标题熬到凌晨,把原本需要三天才能写完的深度分析,压缩成三分钟的短视频,还得在开头加上“这个视频将会改变你的一生”“我很震惊!”这样的话。
“你老了,张军。”张军心底的声音又响了起来,清晰得像有人在耳边说话。这不是疑问句,是陈述句,这些话语非常寒冷,冷得像莫斯科冬天的风,刮在脸上生疼。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,皮肤松弛,眼角有了细纹,手指按下去,能感觉到皮下的脂肪在轻轻晃动。这不是生理上的“老”,是精神上的枯萎–就像他阳台上那盆绿萝,自从他懒得浇水后,叶子一点点变黄,藤蔓软塌塌地垂下来,再也没有过生机勃勃的样子。
两年前不是这样的。那时候,他的国际评论博客还像互联网上的一座灯塔。每天早上醒来,后台能收到几百条留言,有人说“张军同志的分析太透彻了”,有人说“因为你的文章,我开始关注俄罗斯的历史”,还有人把自己拍的莫斯科街景发给她,说“这是我按照你写的路线去的,真的很美”。那时候,他享受那种“权力”–不是职位带来的权力,是用文字和镜头塑造公众认知的快感。
张军记得有一次,他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卫国战争老兵的报道,里面提到一位叫伊万诺夫的老兵,一辈子都在守护着家乡的纪念碑。文章发出去后,有读者专门从国内飞到俄罗斯,找到了那位老兵,还寄给张军一张两人的合影,照片里,老兵握着读者的手,笑得满脸皱纹。那时候,他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,就像在黑暗里点亮了一盏灯,不仅照亮了别人,也温暖了自己。
可现在,希望的灯灭了。
张军拿起桌上的平板,屏幕亮起来,映出他圆润的脸。最新一条视频是三天前发的,标题是“俄乌边境历史溯源: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,百年争端背后的真相”。他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查资料,还翻出了当年在莫斯科采访时的笔记,视频里用了很多老照片,还有他自己拍的边境风景。可后台数据惨不忍睹:播放量刚过五千,评论区只有二十几条留言,还大多是“视频太长了,没看完”“直接说谁对谁错就行”“这个视频也太无聊了”这样的话。
他滑动屏幕,手指在那些评论上轻轻划过,像在触摸一块冰冷的石头。他想起自己为了“迎合”,做过的那些妥协:把“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”改成“3分钟看懂俄罗斯文化”;把“莫斯科地铁的建筑艺术”的视频剪成“盘点莫斯科地铁里的摄影点”;甚至在一条关于俄乌冲突的视频里,故意加入了“中美阴谋论”这样的表述–他知道这话不客观,可当时后台的播放量数据一直在掉,他急了,像个溺水的人,抓住什么都想当成救命稻草。
每一次妥协,都像在他心上划了一刀。白天,他看着上涨的播放量,会有一丝短暂的窃喜;可到了晚上,躺在床上,黑暗里那些被他修改过的文字、被剪辑得支离破碎的镜头,会一遍遍在他脑海里回放。
“坚守良知承受苦难,还是屈从欲望获得解脱?”这个问题像一根尖刺,扎在他的心里,拔不出来,也咽不下去。这两年,他一直试图屈从欲望,可解脱在哪里?没有。反而像陷在泥沼里,越挣扎,陷得越深。他的胃里又开始隐隐作痛,是刚才吃的糖油饼在作祟。他起身走到厨房,打开冰箱,里面塞满了食物:半只酱肘子,一袋速冻饺子,还有昨天买的烤鸭–鸭皮已经不脆了,泛着一层油光。他拿出烤鸭,扯下一块肉塞进嘴里,鸭肉的香味在舌尖散开,可那种满足感只持续了几秒钟,随后而来的,是更深的空虚,像潮水一样,从胃里漫到胸口,压得他喘不过气。
“够了。”他低声说,声音很轻,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不是情绪激动时的脱口而出,是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、无数次自我拷问后,得出的结论–笨拙,却诚恳。他回到客厅,拿起平板,点开自媒体账号的后台。注销账号的按钮在屏幕的最下方,灰色的,像一块墓碑。他的手指悬在上面,停顿了几秒钟–想起第一次发视频时的紧张,想起收到第一条好评时的激动,想起那些因为他的内容而产生共鸣的读者。可这些,都已经成了过去。
他按下了“确认注销”。
屏幕上弹出“账号已注销”的提示,白色的字在黑色的背景上,格外刺眼。那一刻,他突然觉得浑身轻松,像卸下了一块压了他好几年的石头。窗外的都市街巷,好像也失去了之前的压抑色彩,灰蒙蒙的天空里,透出了一丝微弱的光。那些挤在一起的高楼,那些织成网的电线,突然变成了一块巨大的、灰色的背景板–他想逃离这里,逃离这个被数据和算法绑架的世界。
张军决定去环游全国。他需要逃离,需要用身体的移动来对抗精神的停滞。他翻出了衣柜最深处的那个黑色背包,那是他当年在莫斯科当记者时用的,背包的带子已经有些磨损。他把心爱的摄影设备装了进去:一台用了五年的单反相机,两个镜头,还有一个笔记本–不是电子的,是纸质的,封面是牛皮的,已经被磨得发亮。这次,他明确告诉自己:镜头是用来记录“纯净生活”的,不是用来变现的;笔记本是用来写心里话的,不是用来写爆款文案的。
出发前的晚上,他把公寓里的食物都收拾了。糖油饼、酱肘子、烤鸭,还有冰箱里的速冻饺子,都装进了垃圾袋,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。看着垃圾桶里鼓鼓囊囊的袋子,他突然觉得,自己好像扔掉的不只是食物,还有那些用来掩盖空虚的“填充物”。他洗了个澡,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,躺在床上,第一次没有失眠。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,在地上洒下一道细长的光,像一条通往远方的路。
第二天一早,他开着自己那辆用了八年的SUV,驶出了北京。车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变化:高楼变成了低矮的平房,柏油路变成了乡间小道,空气里的雾霾味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泥土和青草的清香。他打开车窗,风灌进来,吹在脸上,带着一丝凉意,却让他觉得格外清醒。他没有设定具体的路线,只知道要往南方走–他在书里看过,南方有很多古镇,青石板路,小桥流水,像一幅水墨画。他想在那里找到一点“纯净”,一点能让他的心静下来的东西。
旅途的第一站,是南方的一个古镇。名字他记不太清了,是在导航上随便找的,据说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可刚到古镇门口,天空就下起了雨。不是倾盆大雨,是那种细密的、连绵不断的雨丝,像无穷无尽的细针,从天上落下来,把整个世界都包裹在一种灰暗的、粘腻的氛围里。
他撑着伞,走在青石板路上。雨水打在伞面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像无数只小虫子在爬。脚下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亮,坑坑洼洼的地方积了水,倒映着路边昏暗的灯笼光–红色的灯笼,被雨水打湿后,颜色变得暗沉,像褪了色的旧伤疤。他拿出相机,想拍一张雨中的古镇,可镜头刚对准前方,雨丝就落在了镜头上,形成一层薄薄的水雾,拍出来的照片模糊不清,像隔着一层毛玻璃。
他擦了擦镜头,再拍,还是一样。那些他想象中的“美”–小桥下的流水,白墙上的青瓦,门口挂着的红灯笼–在雨里都失去了光彩。流水是浑浊的,青瓦上沾着青苔,红灯笼耷拉着,像没精打采的病人。他沿着石板路走了一个多小时,相机里只存了几张模糊的照片,心里的挫败感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他意识到,他无法在潮湿中找到纯净–就像他无法在空虚中找到满足一样。
天黑的时候,他在古镇里找了一家民宿。民宿是老式的四合院,院子里种着一棵桂花树,叶子被雨水打湿后,绿得发黑。房间在二楼,推开房门,一股霉味扑面而来,混合着墙角青苔的味道,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两声。房间里的家具很旧,一张木床,一个掉了漆的衣柜,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。他把背包放在椅子上,走到窗边,推开窗户,雨还在下,桂花树上的水珠顺着叶子滴下来,落在院子的石板上,发出“嗒嗒”的声音。
这声音,和他内心的痛苦节奏完美同步。他想起多年前在莫斯科的冬日里,也是这样的夜晚。那时候,他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寓里,公寓有暖气,晚上很暖和。他会泡一杯热茶,坐在窗边,看着窗外的雪落下来–大片大片的雪花,像羽毛一样,轻轻落在地上,很快就把整个城市变成了白色。雪落的声音很轻,“簌簌”的,能让人的心慢慢静下来。那时候,他刚做完一个关于俄罗斯民间艺术的报道,虽然累,但心里很充实。他会在笔记本上写下当天的感受,字里行间都是对生活的热爱。
可现在,那种平静早就没了。
“你逃不出你的工作和播放数据,张军。你只是换了一个更潮湿的牢笼。”心底的声音又开始嘲讽他,像一把钝刀子,在他心上慢慢割。他觉得饿,不是胃里的饿,是心里的空。他拿出手机,在附近找了一家评分很高的餐馆,点了烤鸭、烧鹅,还有一碗汤。很快,菜就送来了。烤鸭的皮还是脆的,蘸着甜面酱,卷着黄瓜和葱丝,咬下去满口油香;烧鹅的皮是暗红色的,肉质很嫩,嚼起来有淡淡的卤味。他大口大口地吃着,好像想把心里的空虚都填满。
可吃了没几口,就觉得腻了。烤鸭的油粘在嘴角,烧鹅的卤味在舌尖散开,可那种满足感很快就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恶心–不是生理上的恶心,是心理上的。他放下筷子,看着桌上剩下的半只烤鸭和大半盘烧鹅,突然觉得很可笑:他以为换个地方,就能摆脱过去的自己,可到头来,还是在用食物掩盖空虚。
他又想起那个问题:“坚守良知承受苦难,还是屈从欲望获得解脱?”现在,他既没有坚守良知,也没有获得解脱,他只是在苦难中游荡,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。
那天晚上,他在民宿里一夜没睡。雨还在下,“嗒嗒”的声音敲在窗户上,也敲在他的心上。天快亮的时候,他收拾好背包,退了房,开车离开了古镇。车驶出古镇的时候,雨还没有停,后视镜里的古镇慢慢变小,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,消失在雨雾里。
他没有再往南方走,而是调转车头,向西北方向开去。他需要干燥,需要宏大,需要用自然的广阔来稀释内心的拥挤。他想起以前在莫斯科时,看过一部关于中国西北戈壁的纪录片,片子里的戈壁滩一眼望不到边,烈日下的山脉是赭红色的,像被火烧过一样,那种辽阔和苍凉,让他印象深刻。他想,或许在那样的地方,他能找到一点平静。
从南方到西北,车程有一千多公里。他开了两天一夜,累了就停在服务区休息,饿了就吃泡面或者面包。一路上,风景一点点变化:绿色的稻田变成了黄色的草原,低矮的房屋变成了稀疏的蒙古包,空气越来越干燥,风也越来越大。到西北的时候,正好是中午,太阳挂在天上,像一个巨大的火球,晒得皮肤发烫。
他把车停在路边,推开车门,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远处的山脉呈现出深沉的赭红色,像伤口干涸后的血痂,在阳光下泛着暗沉的光。戈壁滩上没有树,只有零星的骆驼刺,贴着地面生长,像一个个小小的灰色疙瘩。风很大,刮在脸上,带着沙子,有点疼。他站在旷野上,张开双臂,感受着风从四面八方吹来–那一刻,他觉得自己很渺小,像戈壁滩上的一粒沙子,微不足道。
这本该是救赎。在宏大的自然面前,个人的痛苦、欲望、成就,都应该变得渺小。可他没有感到轻松,反而觉得更压抑了。他过去的成就–央视记者的身份,国际知名博主的头衔,那些曾经让他骄傲的报道和视频–在这片戈壁面前,都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尘埃。他想起自己为了流量熬夜写文案,为了迎合读者修改观点,为了广告赞助违心推荐产品–那些他曾经以为很重要的东西,现在看来,都像一个笑话。
这种彻底的虚无感,让他更加接近绝望时的非理性冲动。他想大喊,想大哭,想把相机摔在地上–可他什么都没做,只是站在那里,任凭风沙吹打在脸上。
他把车停在路边,拿出相机,对准了远处天空中的一只秃鹫。那只秃鹫飞得很高,翅膀展开,像一块黑色的破布,在蓝天上缓慢地盘旋。他想拍下它,想留住这种苍凉的美。可他按下快门的时候,手抖得厉害,相机在手里晃动,拍出来的照片要么只拍到了秃鹫的一个翅膀,要么就是一片模糊的天空。
他放下相机,看着镜头里自己的倒影–圆脸,双下巴,眼神里满是疲惫和迷茫。“看看你,”他对着镜头里的自己说,声音沙哑,“贪婪的褶皱,嫉妒的尖刺。你贪婪名声,嫉妒那些比你更出名的年轻人。现在,你站在这里,你终于承认了恶的根深蒂固。”
风刮得更紧了,把他的声音吹散在戈壁滩上。他开始面对着空旷的戈壁,对着天上的秃鹫,也对着自己的内心。他问自己,为什么要环游全国?是真的想寻找“纯净生活”,还是只是想找一个借口,逃避现实?是想找到一个可以拍摄“纯净”照片的地方,然后重新开始做博主,继续追逐流量?
“不,我不能再回去。”他对自己说,语气坚定,却带着一丝不确定。他知道,他害怕的不是流量本身,是流量带来的那种“被需要”的感觉–那种每天打开后台,看到无数条留言的热闹,那种因为自己的内容而影响别人的成就感。可他也知道,那种“被需要”是虚假的,是建立在迎合和妥协之上的,像一座空中楼阁,随时都可能倒塌。
在中国西北的那几天,他每天都开车在戈壁滩上转。白天,他看着烈日下的山脉,看着远处的沙丘,看着偶尔路过的骆驼队;晚上,他就把车停在服务区,躺在车里,看着窗外的星星。星星很亮,比北京的星星亮多了,密密麻麻地挂在天上,像撒了一把碎钻。可他还是睡不着,心里的杂念像戈壁滩上的沙子一样,怎么也清理不干净。
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平静,而是遇到了更彻底的“自我”。那些他一直试图逃避的东西–贪婪、嫉妒、虚荣、懦弱–在这片宏大的戈壁面前,都暴露无遗。他像一个被剖开意识肌理的外科医生,直面了潜意识的暗河。宏大带来的不是慰藉,而是对个体痛苦的无限放大。
他必须去一个边缘,一个既能让他远离中心,又能让他找到历史和文化回响的地方。他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那些碎片:奶奶做的红菜汤,爷爷讲的俄罗斯故事,家里墙上挂着的那张黑白照片–照片里,他的奶奶穿着俄罗斯传统的连衣裙,他的爷爷穿着军装,两人站在一棵白桦树下,笑得很开心。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份–第二代中俄混血后裔。奶奶是俄罗斯人,年轻时跟着爷爷来到中国,爷爷去世得早,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。小时候,奶奶经常跟他说俄语,教他唱俄罗斯民歌,给他做列巴和红菜汤。那时候,他对“中俄混血后裔”这个身份没有太多概念,只觉得奶奶的俄语很好听,红菜汤很好喝。
后来,他去莫斯科当记者,俄语成了他的工作语言。他每天用俄语采访,用俄语写报道,可那时候的俄语,只是一种工具,没有了奶奶教他时的温度。他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中俄混血后裔身份,好像那是一个不能说的秘密。他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,害怕别人说他“不纯粹”–既不是纯粹的中国人,也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。
现在,他想找回那个身份。他想回到一个能让他感受到文化归属感的地方。他打开地图,手指在屏幕上滑动,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–室韦。
室韦,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,是蒙古族的发源地之一,也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。他在书里看到过,那里住着很多中俄混血后裔,他们有着蓝眼睛、黑头发,说着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,却保留着俄罗斯的生活习惯。那里有俄式的“小木屋”民居,有红菜汤和列巴,有他童年记忆里的一切。
张军沿着漫长的边防公路(G331)向北行驶。这条路很长,沿着额尔古纳河,一边是中国,一边是俄罗斯。随着纬度的升高,天气越来越凉,空气也越来越干燥。他打开车窗,风灌进来,带着一丝清冽的气息,不像南方的风那样粘腻,也不像西北的风那样灼热。
他穿过了草原。草原上的草已经开始变黄,像一块巨大的金色地毯,铺在天地之间。偶尔能看到几群牛羊,在草原上慢悠悠地吃草,远处有白色的蒙古包,像一朵朵蘑菇,散落在草原上。他停下车,走到草原上,脚下的草很软,踩上去能感觉到泥土的湿润。他深吸一口气,空气里有青草的清香,还有一丝淡淡的牛粪味–那是一种充满生活气息的味道,让他觉得很踏实。
再往前走,草原变成了森林。先是稀疏的杨树,然后是成片的白桦林。白桦树笔直地站在那里,树干是洁白的,像一支支安静的蜡烛,树枝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变黄,风一吹,叶子就“哗哗”地响,像在唱歌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下来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随着树叶的晃动,光影也跟着跳动。
他想起了莫斯科的冬天。那时候,莫斯科的白桦林被白雪覆盖,树干是白色的,树枝上挂着厚厚的积雪,阳光照在雪上,反射出耀眼的光芒。他曾经在一个周末,和同事一起去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,踩着雪,听着脚下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手里拿着热咖啡,心里满是温暖。现在,虽然是初秋,没有雪,但眼前的白桦林,还是让他想起了那种被隔离、被净化的状态。
在到达额尔古纳市后,他没有停留,继续沿G331行驶了约三小时。路边的白桦林越来越密,空气也越来越冷。他打开暖气,车里慢慢暖和起来。他看着窗外,白桦树的影子在车窗外快速闪过,像一幅幅流动的画。
终于,他看到了“室韦镇”的路牌。路牌是蓝色的,下面还有一行俄语–“Шивигова”。他心里一阵激动,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,终于要回到熟悉的地方。
他驶入室韦镇,车开在小镇的路上,路面是柏油的,很平整。街道两旁,全是俄式“小木屋”民居。那些用原木叠砌而成的房屋,散发出松木特有的清香,混合着森林的气息,让他一下子就放松下来。原木是浅棕色的,表面很光滑,缝隙里填着绿色的苔藓,既保暖又防雨。有些房屋的门口挂着一串串晒干的红辣椒和玉米,还有的挂着俄罗斯国旗和中国国旗,在风里轻轻飘动。
他停下车,推开车门,吸了一口冷冽的空气。空气里有松木的清香,还有一丝淡淡的面包香–那是列巴的味道。他沿着街道慢慢走,脚步很轻,好像怕打扰到这里的宁静。
街道上很安静,偶尔能看到几个行人。有老人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晒太阳,手里拿着编织针,在织毛衣;有小孩在路边追逐打闹,嘴里说着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,偶尔夹杂着一两个俄语单词;还有妇女提着篮子,从家里出来,应该是去买东西。他看到一个妇女,有着蓝眼睛、黑头发,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,和他奶奶年轻时的样子很像。
他走到一家小餐馆门口,餐馆的招牌是用中文和俄语写的–“奶奶的红菜汤”。他犹豫了一下,推开门走了进去。餐馆里很暖和,暖气开得很足。墙上挂着很多老照片,有室韦镇过去的样子,有中俄混血后裔的家庭合影,还有一些俄罗斯的风景画。桌子上放着白色的桌布,上面有小小的花纹,很精致。
“您好,请问几位?”一个服务员走过来,笑着问他。服务员也是蓝眼睛、黑头发,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东北方言,声音很温柔。
“一位。”张军说,心里有些紧张。
“那您坐这边吧。”服务员把他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,递给他一本菜单。菜单是中文和俄语对照的,上面有红菜汤、列巴、俄式煎肉、土豆泥……都是他小时候奶奶经常做的菜。
“我要一碗红菜汤,一个列巴,再来一份俄式煎肉。”他指着菜单说。
“好嘞,您稍等。”服务员笑着走开了。
他坐在窗边,看着外面的街道。窗外的白桦树在风里轻轻摇曳,阳光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,反射出温暖的光泽。他拿出相机,对准窗外的白桦林,按下快门。这一次,镜头没有模糊,照片里的白桦树清晰而挺拔,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,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他看着照片,心里一阵温暖–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“纯净”,不是风景的纯净,是内心的平静。
很快,菜就上来了。红菜汤装在一个白色的瓷碗里,汤是深红色的,里面有甜菜、土豆、牛肉,还有一点酸奶油,散发出浓郁的香味。列巴是刚烤好的,外皮很脆,里面很软,上面撒着芝麻和燕麦。俄式煎肉是用猪肉做的,煎得金黄,旁边放着土豆泥和酸黄瓜。
他拿起勺子,喝了一口红菜汤。汤的味道很浓郁,甜菜的甜,土豆的绵,牛肉的香,还有酸奶油的酸,混合在一起,在舌尖上散开。那味道,和他奶奶做的一模一样。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,想起了小时候,奶奶把红菜汤端到他面前,摸着他的头,说“我的孩子,快吃,热乎的”。那时候,他总是狼吞虎咽地把汤喝完,还会把碗底舔干净。
他慢慢吃着,没有像以前那样狼吞虎咽,而是细细地品味每一口食物的味道。列巴的麦香,煎肉的焦香,酸黄瓜的清爽……每一种味道,都让他想起童年的时光,想起奶奶的笑容,想起那些简单而幸福的日子。
“您是从外地来的吧?”旁边桌子上的一位老人笑着问他。老人头发花白,戴着一副老花镜,手里拿着一个列巴,正在慢慢吃。
“嗯,从北京来的。”张军笑着回答。
“来旅游的?”老人问。
“算是吧,也想看看这里的生活。”张军说。
“这里好啊,空气好,人也好。”老人笑着说,“我是第三代中俄混血后裔,爷爷是俄罗斯人,奶奶是中国人。小时候,奶奶也给我做红菜汤,跟你这碗一样香。”
“您一直在这儿生活吗?”张军问。
“是啊,一辈子都在这儿。年轻的时候去北京打过工,可还是觉得这里好。”老人说,“这里安静,踏实,有家里的味道。”
“家里的味道”–这五个字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张军的心门。他终于明白,他一直在寻找的,不是“纯净生活”,也不是“流量”,而是“家的味道”–那种能让他感受到归属感,能让他的心静下来的味道。
吃完饭,他走出餐馆,太阳已经开始西斜。夕阳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,把屋顶染成了金色。街道上,行人比刚才多了一些,有下班回家的人,有吃完饭出来散步的人,大家脸上都带着平静的笑容。
他走到额尔古纳河边,河水很清,能看到河底的石头。河对岸就是俄罗斯,能看到那边的村庄和树林。他站在河边,看着河水缓缓流淌,心里一片平静。他想起了北京的公寓,想起了以前的互联网流量数据,想起了那些迎合和妥协–那些曾经让他痛苦的东西,现在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他拿出相机,对准额尔古纳河,对准河对岸的俄罗斯,对准身边的白桦林,对准街道上的小木屋–他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照片,每一张照片里,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,充满了温暖。他不再想这些照片能不能火,能不能带来流量,只是想把这份平静和温暖,永远留在镜头里。
晚上,他在室韦镇找了一家小木屋民宿。民宿的老板是一对年轻的夫妻,也是中俄混血后裔。老板给了他一间朝南的房间,房间里有一张木床,床上铺着带有俄罗斯花纹的被子,窗户边有一张桌子,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。
他打开窗户,外面很安静,能听到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,还有远处白桦林里的风声。他拿出笔记本,写下了今天的感受:“在室韦,我找到了家的味道。这里的小木屋,这里的红菜汤,这里的人,都让我觉得很踏实。我终于明白,所谓的纯净生活,不是逃离,而是接纳–接纳自己的过去,接纳自己的身份,接纳生活的不完美。”
写完后,他合上笔记本,躺在床上,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一夜,他没有做噩梦,也没有失眠,睡得很沉,像一个孩子。
第二天早上,他被窗外的阳光叫醒。他打开窗户,看到老板正在院子里烤牛肉,空气中弥漫着面包的香味。老板看到他,笑着说:“张军同志,起来啦?快来吃刚烤好的牛肉。”
他走到院子里,接过老板递来的烤牛肉,咬了一口,还是熟悉的味道。他看着院子里的白桦树,看着远处的额尔古纳河,心里突然有了一个决定:他想留在室韦,或者至少,在这里待一段时间。他想好好感受这里的生活,想写一些关于中俄混血后裔的故事,想拍一些关于室韦的照片–不是为了流量,不是为了名声,只是为了记录这份平静和温暖,为了找回那个曾经热爱生活的自己。
他拿出手机,给北京的朋友发了一条消息:“我在室韦,找到了我想要的生活。”朋友很快回复:“那就好,照顾好自己。”
他放下手机,抬头看着天空。天空很蓝,像一块干净的蓝宝石,白云在天上慢慢飘着,像棉花糖。他深吸一口气,空气里有松木的清香,有列巴的麦香,还有额尔古纳河的水汽–那是家的味道,是幸福的味道。
他知道,他的自我突围之路,还没有结束。未来,他可能还会遇到困惑和痛苦,还会想起北京的流量和名声。但他不再害怕了,因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“纯净生活”–不是在镜头里,不是在数据里,而是在心里,在这份平静和温暖里。
他拿起相机,对准院子里的白桦树,按下了快门。照片里,白桦树笔直地站在那里,阳光照在树干上,反射出温暖的光泽。这张照片,他没有存在相机里,而是洗了出来,放在了笔记本的第一页。
这一次,他守住的,是自己的心。
张军沿着室韦镇的街道往额尔古纳河畔走,脚下的柏油路刚被晨露浸过,踩上去带着一点微凉的湿意。街道两旁的小木屋民居挨得不算密,每栋房子之间都留着窄窄的空隙,空隙里种着几株耐寒的雏菊,花瓣是淡紫色的,沾着露水,像撒了一把碎钻。原木搭建的房身上,苔藓沿着木纹的缝隙生长,是深浅不一的绿,把浅棕色的木头衬得愈发温润–那是时光浸出来的颜色,不像北京公寓楼外的瓷砖,冷硬又刺眼。
他走得慢,眼睛忍不住往两边瞟。有的小木屋门口挂着褪色的蓝布门帘,门帘上绣着俄式的缠枝花纹,风吹过时,门帘轻轻晃,能瞥见屋里摆着的原木桌子,桌上可能放着一个玻璃罐,罐里泡着腌黄瓜;有的门口拴着一头棕色的牛,牛低着头啃着门口的干草,尾巴慢悠悠地甩着,驱赶着落在身上的苍蝇;还有的窗户敞开着,飘出一阵俄语歌的旋律,是很老的调子,他没听过,但旋律里的温柔,像奶奶以前哼的摇篮曲,轻轻挠着他的心尖。
空气里的味道很复杂,却格外舒服。有松木的清香–是小木屋本身散发的,混着远处森林里飘来的气息;有烤面包的麦香–应该是哪家在做列巴,甜丝丝的,勾得他肚子有点饿;还有一点河水的腥气–淡淡的,带着湿润的凉意,那是额尔古纳河的味道。他深吸一口气,胸腔里满是这种混合的气息,像把整个室韦的秋天都吸了进去,比在北京吸的雾霾舒服多了,也比南方古镇的霉味清爽多了。
走了大概十几分钟,前面的街道突然开阔起来,额尔古纳河就这样撞进了他的眼里。
河不宽,却很长,像一条蓝色的绸带,绕着室韦镇蜿蜒向远方。河水很清,清得能看见河底的鹅卵石,有的白,有的灰,有的带着褐色的花纹,阳光洒在水面上,碎成一片一片的金箔,随着水流轻轻晃。河面上偶尔有几只白鹭飞过,翅膀掠过水面,留下一圈圈浅浅的涟漪,很快又被水流抚平。
中俄友谊大桥就在不远处,是一座白色的斜拉桥,栏杆上刷着干净的白漆,偶尔有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边境工作人员走过,脚步很轻,像是怕打扰了这里的安静。桥上没有太多游客,只有一两个拿着相机的人,站在桥边拍对岸的风景。张军顺着他们的目光望过去,对岸就是俄罗斯的奥洛契小镇。小镇的房子很低矮,大多是红色的屋顶,烟囱里冒出淡淡的白烟,像一条细细的线,飘在蓝天上。能看到几头黑色的牛在对岸的草地上吃草,还有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小孩,在院子里追着一只黄狗跑,笑声好像能顺着河水飘过来。
他站在河边,看了好一会儿。风从河面上吹过来,带着河水的凉意,吹在脸上,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飘起来。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,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,看到的是灰蒙蒙的天和挤在一起的高楼,风里全是汽车尾气的味道;在南方古镇的时候,风里带着雨的粘腻,吹得人心里发潮;在西北戈壁的时候,风里带着沙子,刮得脸疼。只有这里的风,清清爽爽的,带着河水和草木的气息,吹得人心里发空,却又很踏实。
“看啥呢,老弟?”
一个粗犷的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,吓了张军一跳。他转过头,看见一个男人蹲在河边的石头上,正低着头整理马具。男人穿着一件深棕色的皮衣,皮衣看起来有些年头了,袖口和领口都磨出了浅褐色的毛边,但很干净,没有一点灰尘。他的肩膀很宽,背有点驼,应该是常年干活累的。头发是灰白色的,胡乱地梳在脑后,露出饱满的额头。面部轮廓很深,高鼻梁,深眼窝,眼睛是蓝灰色的,像额尔古纳河的水,带着一点浑浊,却很亮。
张军笑了笑,走过去:“看对岸。看那边的小镇,挺安静的。”
男人抬起头,顺着他的目光望了一眼对岸,然后从旁边的马车上拿起一个玻璃罐,罐子里装着深绿色的腌黄瓜,上面还泡着几瓣蒜。他打开罐子,一股蒜香和醋香扑面而来,他捏起一根腌黄瓜,倒了一杯伏特加,递给张军:“来点?喝伏特加就得配这个,解腻。”
张军摆摆手,指了指自己的肚子:“不了,早上刚吃了列巴,还不饿。再说我也不太会喝酒。”其实他不是不会喝,在北京做博主的时候,为了拉赞助、搞合作,他喝了不少应酬酒,每次都喝得胃里翻江倒海,后来就尽量不喝了。现在看到这罐腌黄瓜,他倒想起奶奶以前也喜欢做这个,奶奶做的腌黄瓜里会放一点糖,没那么酸,更爽口。
男人也不勉强,自己咬了一口腌黄瓜,“嘎吱”一声,听得很清楚。他把罐子放在旁边的石头上,又拿起一个马镫,用一块旧布仔细地擦着上面的锈迹。马镫是铁的,已经有些年头了,边缘都磨圆了。“静?”男人笑了,声音像两块石头撞在一起,粗哑却有力,“这条河底下流的可是历史!你没听过吧?以前啊,这河上全是拉货的船,运皮毛,运茶叶,晚上的时候,船上的灯一串一串的,像天上的星星。现在是静了,可底下的故事还在呢。”
张军没说话,蹲在他旁边,看着他擦马镫。男人的手很大,指关节很粗,手上布满了老茧,有的地方还留着浅褐色的疤痕。他擦马镫的动作很认真,一点一点地擦着每一个角落,好像那不是一个普通的马镫,而是一件宝贝。“你看出你的样子,长得就像我那帮老亲戚,”男人突然开口,眼睛还盯着马镫,“高鼻梁,深眼窝,虽然眼睛是黑的,但一看就不是纯东北人。你也是后裔吧?中俄混血后裔。”
“嗯,第二代。”张军点点头,心里有点惊讶,也有点释然。在北京的时候,没人能看出他的身份,大家只知道他是“张军记者”;在莫斯科的时候,别人只把他当成中国记者,是个外来者。只有在这里,有人能一眼看出他的根。“我叫张军。”
“瓦西里。”男人终于抬起头,伸出手,手上还带着布屑,“五十五了,在这河边待了快三十年了。以前是猎人,现在兼着做点边境巡逻的活,算是半个警察吧。”
张军握住他的手,瓦西里的手很有力,掌心的老茧蹭得他手心有点痒。“忘年交就是这么认识的。”瓦西里豪迈地拍了拍他的肩膀,力道很大,拍得张军肩膀有点疼,却很亲切。他好像一下子就和这个陌生的男人拉近了距离,比在北京和那些合作方应酬时还要近。
瓦西里把擦好的马镫放在一边,又拿起缰绳,开始整理上面的绳结。“我祖母也是俄罗斯人,”他突然开口,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,“她是白俄贵族家里的侍女,十月革命的时候,跟着贵族逃出来的。路上走了大半年,冻饿交加,贵族没撑住,死在了半路上。她一个人走到室韦,快饿死了,被我祖父救了。”
张军屏住呼吸,听他讲。阳光照在瓦西里的脸上,把他的皱纹照得很清楚,那些皱纹里好像都藏着故事。
“我祖父是个猎户,一辈子没娶媳妇,就一个人住在山里。救了我祖母后,就把她带回了家,给她煮了一锅肉汤,我祖母喝了汤,就哭了,后来她说她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汤。”瓦西里笑了笑,眼里带着一点温柔,“后来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祖母不会说中文,我祖父不会说俄语,刚开始他们就靠比划过日子。她教我祖父做列巴,做红菜汤,我祖父教她认山里的草药,教她打猎。慢慢的,她也会说几句中国东北方言了,虽然说得不流利,但够用。”
“我小时候,祖母还在。她总给我讲俄罗斯的故事,讲圣彼得堡的冬宫,讲莫斯科的红场,可她自己也没去过那些地方,都是听以前的贵族说的。她还教我唱俄语歌,就是那种很老的民歌,现在没人会唱了。”瓦西里拿起旁边的伏特加酒瓶,拧开盖子,喝了一口,酒液顺着他的嘴角流下来,滴在皮衣上,留下一个深色的印子,“她到死都没回俄罗斯,也没见过她的家人。她总说,室韦就是她的家,这里有我祖父,有我,有她熟悉的山和河,比俄罗斯还亲。”
张军看着瓦西里,心里有点发酸。他想起自己的奶奶,奶奶也是俄罗斯人,也是年轻时来到中国,一辈子没回去过。奶奶以前也总给他讲俄罗斯的故事,讲她小时候在莫斯科郊外的农场里,和小伙伴一起摘草莓,一起在河边钓鱼。那时候他还小,听不懂,总觉得奶奶的故事没意思,现在想起来,那些故事里藏着奶奶多少的思念啊。
“我们这些长着俄罗斯人的样子的东北人,活得就是个矛盾体。”瓦西里突然说,声音变得很沉,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流,缓慢却有力量,“你说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吗?不知道。说我们是中国人吧,我们长得不像;说我们是俄罗斯人吧,我们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不会说俄语,没去过俄罗斯,连那边的样子都只在河边看过。但我们知道,我们属于这片土地。”
他转过头,眼睛直直地看着张军,蓝灰色的眼睛里带着一种看透人心的锐利:“我认识你,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,你是驻俄罗斯记者,你来这里,是想找回你那十几年莫斯科生活的影子吧?还是想找回,你那被现代社会淹没了的,中俄混血后裔的身份?”
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子,一下子剖开了张军的内心。他愣住了,张着嘴,想说点什么,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的心跳得很快,手心都出汗了。瓦西里的话,比他在北京那几个月的自我思辨还要有穿透力。他以前总以为,自己来室韦是为了寻找“纯净生活”,是为了逃离流量的绑架,可现在他才明白,他真正想找的,是一个身份的锚点–一个能让他知道“自己是谁”的地方。
在莫斯科,他是央视记者,拿着采访本,背着相机,走在陌生的街道上,别人看他的眼神都是“外来者”;在北京,他是自媒体博主,每天盯着后台的数据,为了流量迎合别人,活成了“数据奴隶”,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;可在室韦,他是张军,是第二代中俄混血后裔,是能和瓦西里这样的人坐在一起,听他讲祖母的故事,闻着腌黄瓜的香味,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流水,不用伪装,不用迎合的张军。
他看着瓦西里,慢慢点了点头,声音有点沙哑:“是,我想找的就是这个。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像个飘着的人,没根。现在在这里,我好像有点找到根的感觉了。”
瓦西里笑了,拍了拍他的肩膀:“早该来了。这片土地,认我们这些人。”
两人又坐了一会儿,没再说话,就静静地看着额尔古纳河的流水。阳光慢慢西斜,把河水染成了金黄色,对岸奥洛契小镇的屋顶也变成了金黄色,像撒了一层金粉。远处的白桦林里,传来几声鸟叫,清脆又响亮。张军觉得心里很平静,像被河水洗过一样,干净又通透。
快到傍晚的时候,张军和瓦西里告别。瓦西里把那罐腌黄瓜塞给他:“拿着吧,回去配列巴吃,比你在北京吃的那些零食好吃。”张军推辞不过,只好收下。瓦西里牵着马,慢慢往镇上走,他的背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,像一座沉默的山。
张军拿着腌黄瓜,站在河边,看着瓦西里的背影消失在街道的拐角处,才转身往镇上走。他决定在室韦住下来,至少住一段时间。他想好好感受这里的生活,想听听更多像瓦西里这样的人的故事,想找回自己丢失的身份。
他开始找民宿。室韦的民宿大多是小木屋做的,有的门口挂着鲜艳的招牌,写着“网红民宿”“拍照打卡地”,里面挤满了游客,吵吵闹闹的,张军看了一眼就走了–他不想再回到那种热闹又空虚的环境里。
他走了两条街,终于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看到了一家民宿。民宿的门口没有招牌,只有一块手写的木牌,上面用中文和俄语写着“王光家小木屋”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却很可爱。门口拴着一只黄色的老狗,看到张军过来,只是抬了抬头,又低下头继续睡觉,一点也不凶。门口的台阶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,长得胖乎乎的,很可爱。
张军推开门,走了进去。一股温暖干燥的空气立刻包裹了他,和外面的凉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屋里有一个石头砌的壁炉,壁炉里烧着松木,火焰跳动着,发出“噼啪”的声音,松木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里,比北京公寓里的香薰好闻多了。壁炉旁边放着一个老式的铁皮烤箱,烤箱的门开着一条缝,里面飘出浓郁的麦香–是烤列巴的味道。
“有人吗?”张军喊了一声。
“来啦!”一个年轻的声音从后院传来。很快,一个年轻人从后院走了出来。他大概二十八九岁的样子,个子很高,穿着一件蓝色的格子衬衫,袖口挽到小臂,露出小臂上的一个小纹身,是一棵小小的白桦树。他的头发很短,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,眼睛是浅棕色的,像室韦秋天的树叶。他的脸上带着一点腼腆的笑,看起来很干净。
“您是来住民宿的吧?”年轻人问,口音是流利的东北腔,很亲切。
“嗯,我想住几天。”张军点点头。
“那您算来对地方了,我这地方安静,人少。”年轻人笑着说,“我叫王光,第三代中俄混血后裔。您叫我小王就行。”
“张军。”
王光把他带到屋里,给了他一杯热水:“您先坐会儿,列巴马上就烤好了,刚烤出来的好吃。”他说着,转身走到烤箱边,打开烤箱门,一股更浓的麦香飘了出来。他戴着厚厚的手套,把一个金黄的列巴拿了出来。列巴很大,比张军的脸还大,表面撒着燕麦和芝麻,烤得金黄酥脆,冒着热气。
“吃点列巴吧,刚烤出来的。”王光把列巴放在一个白色的瓷盘里,递到张军面前,又拿来一小罐蓝莓酱和一小碗奶渣,“蘸着这个吃,蓝莓酱是我自己做的,用的是山上的野蓝莓;奶渣是我外婆做的,我们叫它西米丹,有点酸,但是香。”
张军拿起列巴,沉甸甸的,手感很实在。他掰了一块,外皮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里面是松软的面包,带着淡淡的麦香,还有几颗葡萄干,咬下去甜甜的。他蘸了一点蓝莓酱,蓝莓的酸甜和面包的麦香混在一起,味道刚刚好。他又尝了一点奶渣,有点酸,却带着浓郁的奶香,和列巴很配。
他闭上眼睛,慢慢咀嚼着。嘴里的味道,和记忆里奶奶烤的列巴一模一样。他想起小时候,每次奶奶烤列巴,他都会守在烤箱边,等列巴一出炉,就迫不及待地掰一块吃,烫得直甩手,却舍不得吐。奶奶会站在旁边,笑着摸他的头,说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”。那时候的日子,简单又幸福,没有流量,没有数据,只有奶奶的笑容和列巴的香味。
“好吃吧?”王光坐在他对面,看着他,眼里带着一点骄傲,“这是我外婆教我做的,她做了一辈子列巴,味道跟别人的都不一样。”
“嗯,好吃,跟我奶奶做的一样。”张军睁开眼睛,心里有点温暖。
就在这时,后院传来一阵手风琴的声音。旋律很熟悉,是《喀秋莎》。琴声有点生涩,好像拉琴的人不太熟练,但每一个音符都很认真,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,像额尔古纳河的流水,慢慢淌进人的心里。
张军停下了吃列巴的动作,耳朵竖了起来,眼神变得柔和。他以前在莫斯科的时候,邻居家有一个老爷爷,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院子里拉手风琴,最喜欢拉的就是《喀秋莎》。那时候他刚到莫斯科,也没有朋友,每天下午就坐在窗边,听老爷爷拉手风琴,心里会觉得不那么孤单。
“谁在弹手风琴?”张军问。
王光的眼神暗了一下,声音有点低:“是我外婆留下的琴。我外婆去年去世了,这琴就一直放在后院。我和我的朋友们喝点酒就喜欢弹会儿手风琴,虽然弹得不好,但总觉得弹着琴,外婆就还在身边。”
张军心里有点发酸。他看着王光,能感觉到他对外婆的思念。
“我外婆是俄罗斯人,”王光慢慢说,“她年轻的时候跟着我外公来到室韦,一辈子都没回去过。她是个很慈祥的人,就是有点执拗,是东正教信徒,每天餐前都要划十字祈祷,谁劝都没用。”他说着,模仿起外婆祈祷的动作:双手合十,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,嘴里轻声念着俄语的祈祷词,眼神很虔诚。
张军看了看桌上的列巴、蓝莓酱和奶渣,心里突然涌起一股熟悉的感觉。这里的一切–小木屋的原木香味、烤列巴的麦香、手风琴的旋律、东正教的祈祷动作–都和他记忆里的莫斯科,和他记忆里的奶奶重叠在了一起。
室韦不是莫斯科。这里没有克里姆林宫的红墙,没有圣彼得堡的冬宫,没有莫斯科地铁里的华丽壁画。但这里有小木屋,有列巴,有手风琴,有和他一样的中俄混血后裔。这里的文化交融,不是刻意营造的“异国风情”,而是融入在生活里的,是真实的,是温暖的。
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,为了怀念莫斯科,他曾经在网上买过俄罗斯的列巴,买过俄罗斯的手风琴CD,可那些列巴都是机器做的,没有麦香;那些CD里的琴声,没有温度。只有在这里,他才能感受到那种真实的、温暖的“莫斯科影子”。
王光把列巴装了一个纸袋子,递给张军:“您带点回房间吃,晚上饿了可以垫垫。您的房间在二楼,朝南,能看到额尔古纳河,晚上还能看到星星。”
张军接过纸袋子,说了声谢谢。他跟着王光上了二楼,房间很干净,家具都是原木做的,一张大床,床上铺着带有俄式花纹的被子,蓝色和白色的,很柔软。窗户很大,推开窗户,就能看到远处的额尔古纳河,河面上的金箔已经消失了,变成了深蓝色,像一块宝石。
“您要是需要什么,就喊我,我就在楼下。”王光说完,轻轻带上了房门。
张军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的风景。天黑了,镇上的灯亮了起来,都是暖黄色的,像星星落在了地上。额尔古纳河静静地流着,河对岸的奥洛契小镇也亮了灯,一点一点的,像萤火虫。手风琴的声音还在飘,这次不是《喀秋莎》,是一首他没听过的俄语民谣,旋律很温柔,像奶奶的摇篮曲。
他靠在窗边,慢慢吃着列巴。嘴里的麦香,鼻子里的松木清香,耳朵里的手风琴旋律,眼睛里的暖黄灯光和蓝色河水,所有的感官都被填满了。他想起瓦西里的话,想起王光的外婆,想起自己的奶奶,想起在莫斯科的日子,想起在北京的日子。
他终于明白,自己为什么想留在室韦了。
第一个理由,是身份的寻根与重塑。在莫斯科,他是外来者;在北京,他是数据奴隶;只有在室韦,他是张军,是中俄混血后裔,是能和瓦西里、王光这样的人坦诚相待的自己。瓦西里的拷问,让他看清了自己内心的渴望–他需要一个锚点,一个能让他知道“自己是谁”的地方。室韦就是这个锚点,这里的土地,这里的人,都认他,都接纳他。
第二个理由,是感官记忆的重叠与对“莫斯科影子”的怀念。他怀念莫斯科的纯净生活,怀念奶奶的列巴,怀念手风琴的旋律,怀念那种简单又温暖的日子。室韦不是莫斯科,但它用小木屋的香味、列巴的麦香、手风琴的旋律、中俄混血后裔的生活,为他提供了一个情感上的替代品。这里的一切,都能唤醒他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,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热爱生活的样子。
他拿出相机,对准窗外的额尔古纳河,对准镇上的暖黄灯光,对准远处的白桦林,按下了快门。照片里的风景,没有华丽的滤镜,没有刻意的构图,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,充满了温暖。他不需要再为了流量而拍照,不需要再为了迎合别人而修改自己的作品。他只是想记录下这份平静,这份温暖,记录下自己找回根的样子。
晚上,他躺在床上,盖着柔软的被子,闻着被子上的阳光味道和松木清香,很快就睡着了。这一夜,他没有做噩梦,没有失眠,睡得很沉,像一个孩子。梦里,他回到了小时候,奶奶坐在烤箱边烤列巴,他守在旁边,等着吃刚出炉的列巴,奶奶摸着他的头,笑着说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”。
第二天早上,他被院子里的鸡叫声吵醒。他推开窗户,看到王光正在院子里喂鸡,老狗趴在旁边的草地上晒太阳。阳光照在小木屋的屋顶上,反射出温暖的光泽。空气里飘着烤列巴的香味,还有一点牛奶的香味。
他笑了。他知道,自己这次找对地方了。室韦不是他逃避现实的地方,而是他重新开始的地方。在这里,他能找回自己的身份,能找回自己的热爱,能找回那种纯净的、温暖的生活。
他拿起桌上的笔记本,写下了今天的感受:“在室韦,我找到了根,找到了记忆里的温暖。这里的小木屋、列巴、手风琴,还有瓦西里、王光,都让我明白,所谓的纯净生活,不是逃离,而是在熟悉的感官记忆里,找回真实的自己。我想留在这里,好好感受这份生活,好好做自己。”
写完后,他合上笔记本,走下楼。王光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,一碗热牛奶,一块刚烤的列巴,还有一个煮鸡蛋。阳光透过窗户,照在餐桌上,暖洋洋的。
“张哥,吃早餐啦!”王光笑着说。
“好嘞!”张军坐下来,拿起列巴,掰了一块,放进嘴里。麦香在嘴里散开,温暖又踏实。
他知道,他的生活,从这一刻开始,重新变得有意义了。
几天后的一个寒冷的清晨,张军是被冻醒的。凌晨五点,小木屋的窗户缝里钻进来一丝寒气,裹着额尔古纳河的水汽,落在他的脸上。他睁开眼,看到屋顶的原木纹路在晨光里泛着浅棕色的暖光,壁炉里的火已经灭了,只剩下一点余温,空气里还飘着壁炉里松木燃烧后的淡香–不是北京公寓里香薰机喷出来的工业香气,是带着木头肌理的、真实的味道。
他翻起身,套上厚外套,踩着地板上的毛毡拖鞋,走到窗边。推开窗户,冷冽的空气一下子涌进来,带着河水的腥甜和白桦林的清苦,呛得他轻轻咳嗽了一声。远处的额尔古纳河还浸在晨雾里,像一条淡蓝色的丝带,对岸奥洛契小镇的屋顶蒙着一层薄霜,烟囱里没冒出烟,大概还没人醒。河边的草地上,几只早起的鸟儿在跳,翅膀扇动的声音很轻,却能清楚地传到耳朵里。
“柳莺。”他下意识地说出声。这个念头让他自己都愣了一下–他怎么知道这是柳莺?在北京的时候,他连小区里的麻雀和鸽子都分不太清,每天听的不是鸟叫,是手机提示音:“您的视频播放量突破1万”“某某品牌想与您合作”。可现在,他站在室韦的清晨里,竟然能凭着一声鸣叫,叫出一种鸟的名字。
他索性走下楼,王光家的老狗还趴在门口睡觉,见他出来,只是抬了抬眼皮,又把头埋进爪子里。张军沿着河边的小路慢慢走,晨雾在他脚边绕,像一层薄纱。他竖起耳朵,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:柳莺的叫声是“叽叽啾啾”的,又细又亮,像缝衣服的线;树莺的叫声低一点,带着“咕噜”的尾音,像含了一口水;还有啄木鸟,“笃笃笃”地敲着树干,节奏很稳,像老式挂钟的摆锤。
他数着,一只、两只、三只……到第七只的时候,他停下脚步,靠在一棵白桦树上,心里突然涌起一阵震撼。过去十年,他能精准识别出二十种视频剪辑工具的用法–这些东西像刻在他脑子里的公式,张口就能说出来。可现在,他能识别出的是二十种鸟的叫声,是自然里真实的声音,是生命的声音。
“这才是活着啊。”他对着空气轻声说。风从河面吹过来,摇了摇白桦树的叶子,叶子上的霜花掉下来,落在他的手背上,凉丝丝的,很快化了。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,每天坐在电脑前,眼睛盯着后台数据,心脏跟着播放量跳,高了就兴奋,低了就焦虑,像个被数据操控的木偶。那时候的他,感官是麻木的:吃美食只知道填肚子,连和朋友聊天都在想“这话能不能做文案素材”。可现在,他能闻到风里的霜味,能听出鸟叫的区别,能摸到树皮的粗糙–他的感官正在被净化,被重新校准,像一台蒙尘的相机,终于被擦干净了镜头。
张军走了快一个小时,晨雾慢慢散了,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爬出来,把河水染成了金红色。他看到瓦西里骑着马从远处过来,马背上挂着猎枪和水壶,皮衣的毛领上结着霜。
“张军!早啊!”瓦西里在马上喊,声音还是那么粗犷。
张军挥挥手:“瓦西里大哥,您这是去打猎?”
瓦西里勒住马,跳下来,拍了拍马脖子:“去看看驯鹿群,前几天下雪,怕它们跑远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?带你看看真正的林子。”
张军眼睛亮了亮:“好啊!”
瓦西里从马背上拿下一件旧皮衣:“穿上,林子里比河边冷。”
张军接过皮衣,套在自己的外套外面,皮衣很重,带着瓦西里身上的烟草味和松木味,很暖和。两人骑着马往林子深处走,马蹄踩在落满松针的地上,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。瓦西里指着地上的脚印:“看,这是驯鹿的,昨天刚踩的,你看这蹄印的形状,是母鹿,带着小鹿呢。”
张军蹲下来,仔细看那些脚印:比马蹄小,边缘有分叉,印在松针上,很清晰。“您怎么能分清是母鹿还是公鹿?”
“看蹄印大小,听叫声。公鹿叫得粗,母鹿细。”瓦西里笑了,“就像你们城里人看电脑,我们看这些脚印,都是吃饭的本事。不过我们这本事,靠的是林子,你们那本事,靠的是机器,不一样。”
张军心里一动:“您觉得哪种好?”
“各有各的活法,”瓦西里骑着马往前走,“但我觉得,靠林子踏实。你对林子好,林子就给你东西:驯鹿的肉,松木的柴,野果的酱。靠机器的话,机器要是停了,你还剩啥?”
这句话像一颗石子,投进张军的心里,漾起一圈圈涟漪。他想起自己注销视频账号的那天,看着“账号已注销”的提示,心里空落落的–他突然发现,除了“博主”这个身份,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了。在北京的那些年,他没交下几个真心朋友,没好好陪过家人,连自己的爱好都丢了–他以前喜欢摄影,是因为喜欢捕捉真实的瞬间,可后来,摄影变成了赚钱的工具,镜头里的人不是人,是“财富密码”。
“您说得对。”张军轻声说。
两人走到林子深处,看到一小群驯鹿,大概七八只,棕色的皮毛上沾着松针,正低着头啃地上的苔藓。瓦西里从马背上拿下一个布袋,里面装着盐:“驯鹿喜欢吃盐,给它们撒点,它们就不会跑太远。”他把盐撒在地上,驯鹿们围过来,低头舔着,发出“啧啧”的声音。
张军拿出相机,镜头对准驯鹿。他没有急着按快门,而是等着:等一只小鹿抬起头,眼睛看向镜头;等阳光穿过树枝,落在驯鹿的皮毛上,映出金色的光。他按下快门,“咔嚓”一声,声音在林子里很轻。他看着相机里的照片,小鹿的眼睛很亮,带着好奇,皮毛上的光很暖–这不是他以前拍的“新闻图”,没有夸张的滤镜,没有耸动的标题,可他看着,心里却比以前涨粉十万的时候还开心。
“这才是拍照啊。”他心里想。不是为了别人看,是为了自己喜欢,为了留住这一刻的真实。
从林子里回来,已经是中午。王光正在院子里烤列巴,看到他回来,笑着喊:“张军,快尝尝,今天加了野蓝莓,甜得很!”
张军走过去,拿起一块刚烤好的列巴,咬了一口,蓝莓的酸甜混着麦香,在嘴里散开。“好吃!比昨天的还香。”
“我外婆以前说,列巴里加野蓝莓,是为了让日子甜一点。”王光擦了擦手上的面粉,“对了,张哥,你不是想租个小木屋吗?我邻居家有一间,空了半年了,带壁炉,还能看到河,要不要去看看?”
张军眼睛一亮:“真的?现在能去吗?”
“走,我带你去。”
邻居家的小木屋在镇子的西边,离河边不远。推开院门,里面有一个小院子,种着几棵苹果树,叶子已经落了,枝桠光秃秃的。小木屋的门是深蓝色的,上面刻着俄式的花纹,推开时“吱呀”一声响。
走进屋里,一股淡淡的霉味飘过来,不过很轻,通风几天就能散。房间很大,分里外两间,外间是客厅,有一个石头壁炉,里间是卧室,窗户朝南,推开就能看到额尔古纳河。“你看这壁炉,冬天烧松木,屋里能到二十多度,比暖气还舒服。”王光指着壁炉里的烟道,“我帮你检查过了,烟道通着,没问题。”
张军走到窗边,看着外面的河,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踏实感。“就这间吧,多少钱一个月?”
“都是朋友,你看着给,别让我亏就行。”王光笑着说,“我帮你收拾,下午就能搬过来。”
下午,张军把自己的东西从王光家搬过来。摄影器材装了两大箱:单反相机、三个镜头、三脚架、备用电池。他把相机摆在窗边的桌子上,镜头对着河。他又拿出一块毛毡,铺在桌子上,把笔记本放上去–他想在上面写室韦的日子,写鸟叫,写驯鹿,写瓦西里和王光的故事。
王光帮他生壁炉,找了几块干松木,塞进壁炉里,用火柴点燃。火苗慢慢起来,舔着松木,发出“噼啪”的声音,热气一点点扩散开来,屋里的霉味渐渐被松木的香味取代。“好了,晚上冷了就添柴,别让火灭了。”王光拍了拍手上的灰,“有事就喊我,我家离得近。”
张军送王光到门口,看着他走远,然后关上门,靠在壁炉边。火光照在他的脸上,暖烘烘的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,这些天在室韦,他没再像以前那样暴饮暴食,每天吃的是列巴、红菜汤、腌黄瓜,都是简单的食物,却很舒服。他想起在北京的时候,用食物填肚子,其实是在填心里的空,可越填越空。现在,心里的空被壁炉的火、河边的风、鸟的叫声填满了,反而不觉得饿了。
“这不是逃避。”他对着壁炉的火说,像是在说服自己,“是试炼。以前在虚拟世界里拷问人性,现在在真实生活里找答案。生存的意义,不是流量,不是名声,是能听见鸟叫,能摸到松木,能和瓦西里一起看驯鹿,能吃王光烤的列巴–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。”
接下来的几天,张军彻底融入了室韦的生活。每天清晨去河边听鸟叫,上午跟着瓦西里去林子转,下午要么在屋里整理照片,要么帮王光修小木屋。王光教他用松木楔:“先把木头削成楔子,要尖一点,然后对准木缝,用锤子敲进去,敲实了,冬天就不会漏风。”张军拿着锤子,一下一下地敲,手很快就酸了,楔子却总歪。王光笑着说:“别急,慢慢来,手上的活得练,就像你拍照,得练才能找准角度。”
张军看着自己敲歪的楔子:“以前总想着快,现在才知道,慢一点才能做好。”
有一天清晨,他起得特别早,四点多就出门了。天上还挂着星星,河边结着薄冰,踩上去“咯吱”响。他沿着白桦林里的栈道走,寒风呼啸着穿过树林,像在唱歌。栈道上结着霜,很滑,他走得很慢,每一步都很小心。
走到栈道中间,他看到一棵白桦树的叶子上凝结着霜花。霜花很细,像羽毛,又像蜘蛛网,贴在叶子上,在晨光里泛着银光。他停下来,拿出相机,蹲在地上,调整焦距。风很大,吹得相机有点晃,他屏住呼吸,手稳了稳,按下快门。
“咔嚓。”
照片里,霜花的纹路清晰可见,叶子的脉络藏在霜花下面,像隐约的血管。他看着照片,心里突然涌起一种久违的快乐–不是涨粉的快乐,不是赚钱的快乐,是纯粹的、创作的快乐。就像他刚当记者的时候,在莫斯科拍下第一张克里姆林宫的雪,那种激动和满足。
“原来我没忘记拍照。”他笑着说,眼里有点湿。
他开始用镜头记录室韦的日常:俄罗斯人做果酱的老方法,王光现在还在沿用–把山上采的野蓝莓洗干净,放在铁锅里,加一点糖,用小火慢慢熬,熬到果酱变得粘稠,冒着泡泡;瓦西里骑马追驯鹿时的背影,皮衣在风里飘,马鬃飞扬,像一幅油画;王光用松木楔修补小木屋时的样子,眉头皱着,很认真,锤子敲下去的力度刚刚好,楔子稳稳地嵌进木缝里。
他的相机里,不再是精心设计的构图,不再是夸张的滤镜,而是真实的生活:果酱熬糊了一点,王光皱着眉刮掉;瓦西里追驯鹿时摔了一跤,笑着爬起来;王光去世的外婆外婆留下的手风琴,王光弹错了一个音,吐了吐舌头。这些不完美的瞬间,却比任何“爆款图”都让他心动。
“我终于回到摄影师的本质了。”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,字迹很稳,不像以前写文案时那样潦草。
一周后,张军把租的小木屋收拾好了。外间的客厅里,他摆了一张原木桌子,上面放着相机和笔记本;壁炉里总烧着松木,屋里暖暖的;墙上挂着他拍的照片:额尔古纳河的晨雾、白桦林的霜花、瓦西里的马、王光的列巴。里间的卧室里,他铺了厚厚的床垫,盖着王光妈妈织的羊毛被,晚上睡得很沉。
他决定去看看镇上的百年东正教教堂遗址。瓦西里跟他说过,那是室韦的中俄混血后裔们的精神象征,以前外婆还活着的时候,每个周日都会去祈祷。“教堂的壁画快掉光了,最近来了个姑娘,从圣彼得堡留学以后回来的,在修壁画。”瓦西里说,“那姑娘也是混血,跟你一样,在找自己的根。”
张军下午出发,沿着街道往教堂走。教堂在镇子的东边,离河边不远,是一座小小的小木屋建筑,屋顶的十字架已经歪了,墙体斑驳,露出里面的原木,上面爬满了苔藓。推开教堂的门,一股带着历史锈迹的寒意涌进来,空气里混着松木和苔藓的味道,很沉。
教堂里很暗,只有几扇小窗户透进光来。墙壁上画着壁画,大多已经模糊了,只有几处还能看到颜色:圣徒的长袍是深蓝色的,光环是金色的,却都裂着缝,像老人脸上的皱纹。
他看到一个女人站在壁画前,背对着他。她穿着深蓝色的修身工装,袖口沾着石灰粉和颜料,头发扎成一个马尾,露出白皙的脖子。她手里拿着一支细毛笔,正对着壁画上一处模糊的地方,一点点填色。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,落在她的侧脸上,勾勒出深邃的轮廓–高鼻梁,深眼窝,眼睛是浅棕色的,像额尔古纳河的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