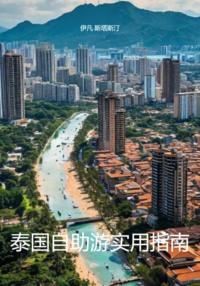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
裂隙奇缘与丝娃娃:瓷偶的幻世之旅 18+

裂隙奇缘与丝娃娃:瓷偶的幻世之旅 18+
第一章 瓷中寂寥
作坊里的寒意别具一格,浸透着老木料、亚麻籽油以及一种沉静而凝练的忧郁气味。安东用手掌拂过刨子的斜边,掸开一片轻薄得几乎没有重量的刨花。它悬空卷曲了一下,悄然飘落在覆盖着经年木屑与灰尘的地板上。窗外,十二月圣彼得堡的暮色在四点就已将白昼埋葬,街灯透出幽蓝的光,透过凝霜的玻璃,在墙上投下台钳、锯子和未完成画框的奇诡暗影。

那个衣柜犹如一艘外星飞船,停在作坊中央。厚重,橡木材质,表面剥落的漆层呈现出凝固血痂般的暗红色。玛莎阿姨的委托:“把它弄得漂亮点,安托申卡,要过节了。这是外婆的,记得吗?”安东记得。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曾躲进它最下面的抽屉里,将樟脑丸和旧信件的味道当作时光本身的气息。如今时光早已挥发殆尽,只留下被遗忘的腐朽气味。
他拉开了最后一个,也是最深的一个抽屉。那个总是卡住的抽屉。底部垫着一张1978年的褪色旧报纸。报纸下面–出乎意料的空旷,而在那空旷之中……有一件东西,用一块堪察加桌布残片包裹着。
安东展开布料。随即,他僵住了。
瓷器。冰冷,无瑕的洁白,却不刺眼。在昏沉的光线中幽幽流转,宛如一颗遥远的星球。这是一个玩偶。一位身着刺绣、但明显已显陈旧的丝质旗袍的女子,旗袍是褪了色的桃红。面容–并非现代玩偶那种蜡制般的甜美面具,而是极为细腻、近乎带着病态美感的作品。高颧骨,微挑的眼角,眼帘半垂,仿佛她在小憩,抑或沉浸在深深的哀愁之中。嘴唇–一枚小小的贝壳,带着细微的弧度,不是微笑,也不是愁容,像一个凝固的词。双手纤细的手指交叠于膝上。其中一只手的拳头微微握起,仿佛曾握着什么东西,如今却已然忘却。
安东,一个习惯了物件、习惯它们的结构和破损之处的人,忽然感到一阵无措。他捧起她,并非像对待一件物品,而是像对待一个脆弱的生命。举起来。重量出乎意料,沉甸甸的,凝聚着,仿佛有生命。
就在那时,他与她的目光相遇。
眼睛是画上去的。仅仅是深色的釉彩。但那眼瞳的位置,釉层之下的深邃……它们在凝视。并非凝视虚空。是在凝视他。穿透他。在这瓷偶女子身上,禁锢着一种如此浓稠的寂静,浓稠得足以令人窒息。她所散发出的那种寂寥,不是孩童的委屈,而是一种成年人的、因长久在黑暗中等待而孕育出的疲惫厌倦。
“你从哪儿来?”他低语。作坊吞没了这声低语。
他不是收藏家。那种“可爱玩意儿”与他格格不入。但他无法移开视线。他将她安置在靠近一排染色剂罐子的架子上。在桐油和金属刷之间,她显得荒诞不经,却又……恰如其分。仿佛她这些年来等待的,正是这样一幅景象。
突然,一阵门铃声让他打了个激灵。时间到了。琐事来了。
玛莎阿姨裹挟着一股寒气和“红色莫斯科”香水的旋风闯进了作坊。
“怎么样,还活着呢,隐士?衣柜好了没?哎呀!”她忽然噤声,死死盯住架子。“这又是什么漂亮玩意儿?外婆的?”
“在抽屉里找到的。”安东闷声回答,侧身挡在她和架子之间,仿佛在保护这个发现。
“有点吓人呢,”玛莎阿姨嗤了一声,“眼睛空落落的。你肯定得扔了吧,占地方。你还是说说,衣柜过节前能弄好吧?客人们要来了!”
她滔滔不绝地谈论客人、菜单,以及必须买套新餐具,因为旧的“彻底过时了”。她的话语像一群麻雀:喧闹、空洞,啄食着注意力的碎屑。安东点着头,目光却越过她,落在瓷偶身上。她那瓷质的面容无动于衷。这样的喧嚣,她一百年前就听过了,而且,大概正以那种静默的、洞悉一切的方式,蔑视着它。
玛莎阿姨走了,许诺明天会带来她烤的杏仁饼干,声称“除了她,没人能烤得对味”。门砰地关上。寂静回归,但此刻已然不同。它变得充盈。
安东用抹布擦了擦手,走到窗边。邻近的楼栋又亮起一串灯饰。闪烁。明灭。一种试图制造奇迹的廉价尝试。他叹了口气,转过身。目光再次撞上那个瓷偶女子。撞见她孤零零置身于铁器和瓶罐之间的身影。
于是,他做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举动。他拿起那盒被玛莎阿姨强塞来、又被他丢在角落的灯饰串。老式的,“杜拉铝”材质,带着粗笨的彩色灯泡。他笨拙地,钩扯着房梁上旧有的钉子,沿着作坊的周边挂起了灯串。插上电源。
灯泡开始闪烁,发出黄、红、绿的光。粗粝,刺眼,俗气。光芒映照在凝霜的窗玻璃上,映在刨子光滑的侧面,映在清漆罐子上。也映入了瓷偶的眼中。
接下来发生的才真正怪异。光线并未在釉面上嬉戏。它仿佛陷进了那双绘制眼眸的深处,在其中点燃了微小的光点,如同幽暗水底的遥远星辰。刹那间,安东觉得她的姿势似乎有了变化。肩膀似乎微微舒展。紧握的拳中,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颤动了一下。
他揉了揉鼻梁。是疲倦。加工橡木总是很耗神。眼睛发涩,大脑便开始描绘奇迹。
但在关灯上楼,回到他那冰冷的公寓之前,他朝瓷偶女子点了点头。完全自然而然,如同对邻居示意。
“好吧,”他轻声说,“你就待在这儿。至少这里,肯定不会有人把你扔掉。”
他走了出去,咔哒一声关了灯。灯串在黑暗中继续闪烁,将黑暗染上节日般却又令人不安的色调。而在这些明灭的光点中,架子上那端坐的身影,已不再仅仅像一个玩偶。她像一位守卫。或一名囚徒。在刚刚开始缓慢流淌的新年之夜那红色、绿色、黄色的幽暗里,等待着她时刻的来临。
第二章 现实的裂痕
十二月三十一日不是一天,而是一条漫长、灰色的绝望带。安东爬出工作室,仅仅是为了去便利店买一罐橄榄沙拉、一瓶廉价香槟和一袋饺子–“以示应景”。城市在狂欢,一种不自然的、歇斯底里的狂欢,如同高烧的病人。到处是黏腻的金箔亮片、强颜欢笑、陌生人高喊“新年快乐”–到了第二天,这些人连“你好”都不会说。安东低着头走着,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,误闯了他人的仪式。
整个晚上,他都呆坐着盯着电视。玛莎阿姨做的菜–就是那种杏仁饼干,酥脆完美–原封未动地放着。它散发着香草和人情债的味道。安东觉得每一次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都敲打在自己的太阳穴上。钟鸣即是终结。又一年坠入了记忆的无底深井,除了散落工作室地上的刨花和一种寂静、莫名的惆怅,什么也没留下。
当屏幕上的人群开始欢笑,喧嚣四起时,他关掉了电视。公寓里坟墓般的寂静突然变得震耳欲聋。他拿起酒瓶和酒杯,下楼去了工作室。
这里不一样。安静,但不空洞。他的工具在各自的套子里沉睡。空气里弥漫着木料的气味和某种隐约的承诺。而在架子上,此刻被那不再闪烁、只发出稳定光芒的灯串照亮着的,是她。瓷偶女子。裂隙库妮娅。
安东在她对面的凳子上坐下。倒上香槟。闪烁的气泡升起,然后破裂。
“那么,”他的声音在这寂静中显得沙哑而迟疑。“就剩我们俩了。我留下,是因为无处可去。你留下,是因为无人带你走。”
他朝她的方向举了举杯。一个可笑的姿势。但在这一刻,这似乎是唯一诚实的举动。
“为了那些不在我们身边的人。”安东说了一句老掉牙的祝酒词。然后,直视着她那双画出来的眼睛,补充道:“也为了那些……至今还无人在侧的人。”
他喝了一口。酒中的气泡刺激着喉咙。尴尬被一种奇怪的坦率所取代。他开始说话。轻声地,断断续续地。说起父亲工作室的气味。说起修复那些终将消亡的物件有多么奇怪。说起玛莎阿姨和她那永不停歇、忙忙碌碌地追求“正确”节日的劲头。说起那种感觉–生活正呼啸而过,而他却站在路边,只是看着别人的灯火飞驰。
“那又是谁把你锁进了抽屉?”他终于问道。“是让谁厌倦了?是坏了吗?还是仅仅……不再被相信了?”
他伸出手,并非要去触碰,只是想用手指在距离她瓷质脸颊一厘米的空气中划过。就在这时,他的手肘碰到了杯沿。一滴香槟,金灿灿的,活生生的,飞溅而出。
一切发生在瞬间。那滴液体没有落在架子上。它落在了她交叠的双手上。并且没有滚落,没有流散。它仿佛被釉面吸了进去。与此同时,他们头顶的灯串爆发出耀眼的白色光芒,迫使安东闭上了眼睛。一声轻微但清晰的“咔”声响起–就像水洼表面的冰壳碎裂。
当光线恢复正常,安东睁开了眼睛。
似乎没什么变化。玩偶还在原处。但是……在她交叠的手背上,酒滴落下的地方,现在出现了一道极细、几乎看不见的裂纹。不是缺口,而是一道裂纹,像蛛网。而且,灯串不再闪烁欢快的五彩光芒。它稳定地亮着,发出温暖、琥珀色的光。
安东的心重重地撞了一下肋骨。他站起来,踉跄后退。“是疲劳。空腹喝酒。该睡觉了。”
他几乎是跑着上了楼,没有关掉工作室的灯。锁上门。倒在床上,瞬间便沉入睡眠,如同陷入泥沼。
他梦见自己站在一座无边花园的边缘。但花园很怪异:树木由泛黄的图纸卷曲而成,枝头悬挂的不是果实,而是旧钥匙和破碎的眼镜。在碎贝壳铺成的小径上,跑动着一些模糊的身影,摇摇摆摆,眼睛像闪亮的珠子。它们急切而贪婪地啃咬着什么。而在花园中央,一棵巨大的树下–树枝缠绕着发光的银丝–站着那位身着枯桃色长袍的女子。她是活的。而且正直视着他。没有呼唤。没有引诱。只是知道他在那里。她的嘴唇翕动,但没有发出声音,取而代之的是一缕带着字迹的绸带在空中飘荡……
安东被一阵刮擦声惊醒。
真实的,物理的刮擦声。吱嘎声。窸窣声。声音来自楼下,工作室。
他跳起来,抓过旧睡袍披上。血液在耳中轰鸣。他拿起一把沉重的活动扳手–手边第一件工具。下楼时,冰冷的镶木地板灼烧着他的赤脚。
工作室的门虚掩着。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关了门。心脏狂跳到了嗓子眼。
他推开门。琥珀色的灯光充满了房间。一切都各就各位。但是……
但是架子上没有玩偶。
安东转过身。她站在大窗户旁,倚着玻璃。她瓷质的侧影朝向夜晚的城市,朝向别人窗户里零星孤寂的灯火。她在看着飘落的雪。
这不可能。他走近些,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是的,她站着。虽然不稳,但确实站着。怎么站的?谁干的?
接着,他看到了第二件事。在地板上那层薄薄的灰尘上–他已一周没打扫–从架子到窗户,有一串细小的足迹。微小的,清晰的,像是爪印。但不是鸟的。也不是猫的。足迹有四个趾,带尖锐的小爪痕,足迹之间,还有一道细细的拖痕,仿佛拖着一条尾巴。
一股寒意如冰针般刺穿安东的脊柱。他在玩偶旁边跪下来,不敢触碰她。他仔细查看那些足迹。有很多。它们在架子周围逡巡,仿佛在寻找什么,然后,像是下定了决心,将它们的发现拖到了窗边。
他抬起目光,望向那张瓷质的脸。手上的裂纹现在像一道伤口。而在她那不变的、画出来的眼睛里,映着窗外飘落的雪花,他读出的不再是孤独的寂寥。
他读出的是期待。
她在等待。不是等他。她在等某个别人。而这些留下足迹的生物,要么是在帮她,要么–这更可怕–是在监视她。或者监视他。
安东小心翼翼地,用双手像捧起圣物一样,拿起玩偶,将她放回架子。他的手指在她底座、长袍的褶皱处摸到一点粗糙的东西。他仔细看去。是一点干涸的碎屑,一小粒。他小心地把它取下来。这不是瓷,也不是灰尘。这是一点干涸的杏仁饼干屑。
耳中的轰鸣变得震耳欲聋。他转过身,审视着工作室角落的阴影。灯串散发着稳定的光,但现在这光芒显得不祥,只从黑暗中凸显出尖锐的棱角和深不见底的漆黑。
他没有关灯。相反,他在凳子上坐了下来,背靠墙壁,以便能同时看到门、窗户和放着瓷偶女子的架子。他把活动扳手放在膝盖上。
就这样,在紧张的寂静中,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爆竹声和警笛呜咽,安东迎来了新年的黎明。他明白,刚刚结束的不仅是一个旧年。旧的生活也结束了–在那个生活里,物件只是物件,梦境只是梦境。
现实出现了裂痕。而现在,某种别的东西正从裂隙中渗漏出来。
第三章 地板下的时啮兽
首先消失的是钥匙。不是丢了–是消失。安东晚上把它们放在工作室门边的矮柜上,早上只看到漆面上有一道细细发亮的划痕。他没在意:常有的事。滑下去,掉到家具后面了。
接着失踪的是那块便宜但可靠的手表。他为了把手伸进衣柜窄缝而摘下表,放在工作台上。转身去拿胶水的功夫–表就不见了。胸膛里泛起一阵冰冷、腻烦的感觉。
然后,记忆开始褪色。
他试图回忆塔尼娅的脸,他大学时的初恋。以前,她清晰的形象会浮现在眼前:含笑的灰眼睛,唇上的痣,习惯猛地一甩头撩开刘海。现在–只剩一片模糊的斑块。五官比例扭曲走样,像没揉好的面团。他能记起她的声音,她说的话,但脸庞本身却溜走了,仿佛被橡皮小心翼翼地擦掉了。
他开始丢失旋律。父亲工作时哼唱的心爱歌曲–现在脑子里副歌的部分空空如也。他搜索、聆听几十首曲子,但没有一首听起来“对味”。这就像截肢后的幻痛–你确切地知道它存在过,却再也无法感受。
安东给自己煮了咖啡,望着窗外的雪,心想:“早期健忘症。压力。孤独在侵蚀大脑。”这是个方便的、带点医学常识的解释。他甚至上网查了查症状。几乎带着解脱感准备给自己下诊断。
但他那工匠的、一丝不苟的天性起来反抗了。东西不会凭空消失。记忆不会自己蒸发。总该有个原因。物质的原因。
他开始注意到细节。早晨,踢脚线旁的地板上–有一片微小、仿佛被啃咬过的刨花,不是他用的木料。工作室角落里–有一小团灰色尘埃,不是木屑。还有气味。一丝微弱、难以捕捉的霉味,混合着陈年泥土和某种类似苦艾的苦涩气息。这气味在夜间出现。
还有玛莎阿姨。她的饼干。
“安托什,你为什么不吃?我花了心思的!”她责备道,指着没动过的盒子。
他掰了一小块。完美的质地,正宗的杏仁。但入口却毫无味道,如同灰烬。它不带来愉悦,只有一种沉重、阴郁的饱腹感。仿佛揉进面团里的不是食材,而是义务感和对这义务的厌倦。
一天,他工作到很晚,听到了那个声音。一种轻微而急促的刮擦声。不是金属的,而是……像骨头。或者爪子。声音来自地板下面。就在他的工作台正下方。
安东僵住了。心脏狂跳。他慢慢地、无声地垂下视线,望向地板之间的缝隙。一个影子一闪而过。小小的,敏捷的。两点针尖般的微光闪过,如同深海鱼的眼睛。不是反光。是从内部发出的一种冰冷、暗淡的绿光。
他没有喊叫。另一种机制在他体内启动–工匠的机制,需要查明故障所在。第二天,他去了商店,买了一个小巧但灵敏的带夜视和运动传感器的摄像头。把它安装在架子上,对准裂隙库妮娅(他越来越多地在心里这样称呼她,用梦中的名字)所在的位置以及踢脚线前的区域。
他检查了画面。清晰,黑白。一个 devoid of 色彩和幻觉的世界。
夜晚。安东坐在楼上的公寓里,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。屏幕分成了两半:左边是工作室的静止画面,右边播放着关于恐龙的纪录片–为了抵御寂静。他正开始打瞌睡,这时左边屏幕上的画面起了变化。
图像边缘出现了一道红色标记。运动传感器被触发了。
安东点击窗口,将其全屏展开。屏住了呼吸。
先是踢脚线边上的那条窄缝–看起来连老鼠都钻不过去的地方–冒出了一个……脑袋。细长,覆盖着短而黏结的灰色毛发。圆圆的、粗野的耳朵。长长的、黄白色的门齿从上唇下突出来。还有那双眼睛。小小的,离得很近,散发着暗淡、病态的绿光。这生物嗅了嗅空气,然后拖出了它短腿、敦实的身躯,后面是一条几乎光秃、带鳞的长尾巴。它有一只大老鼠大小,但动作并不慌促,而是有条不紊,近乎庄严。
土拨鼠。但某种……不对劲的土拨鼠。扭曲的。仿佛是根据某人对土拨鼠模糊而厌恶的记忆捏造出来的。
接着,第二只爬了出来。第三只。它们对刨花、工具视若无睹。它们只被一样东西吸引。
玛莎阿姨的饼干盒,被安东心不在焉地留在了矮凳上。
它们包围了它。但没有啃咬纸盒。其中一只用后腿站立,前爪搭在盒子边缘,然后……嗅闻。长久地,深深地。它的两肋剧烈起伏。其他几只也效仿起来。它们不吃。它们在吸入。随着它们每一次有节律的吸气,黑白画面上的颜色似乎变得更加黯淡,阴影也更加浓稠、凝固。它们吮吸的不是碎屑,而是气味本身。那锁住了所有无聊、所有勉强营造的节日气氛、所有烘焙者未曾消解的烦闷的气味。
安东看得呆住了。他关于啮齿类动物的理论彻底崩塌了。它们不是小偷。它们是寄生虫。但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寄生虫。
接着,那只领头的、最大的家伙猛地转动它那迟钝的脸。它那绿色的珠子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摄像头镜头。直盯着安东。它仿佛能透过屏幕看到他。它发出一声低沉的、咕噜咕噜的喉音。
随即,整群生物,如同听到命令,齐刷刷地转身,不是冲向踢脚线,而是冲向裂隙库妮娅所在的架子。
安东的心猛地一抽。他已经跳起来准备冲下楼,却又停住了。
土拨鼠们没有爬上架子。它们在架子前围成半圆,用后腿站立,然后静止不动。凝视着。鼻子抽动着。它们仿佛在研究她。在评估。一只伸出爪子,但没有触碰–仿佛在害怕,或者无法逾越一道无形的屏障。在她瓷质的脸上,在摄像头微小的反光中,看不清表情。但安东隐约觉得,她正居高临下地看着它们,眼神里带着第一天看玛莎阿姨时那种同样的冰冷轻蔑。
然后,领头者又咕噜了一声,时啮兽们仿佛心满意足,瞬间消失在踢脚板下的缝隙里,融入了它们来的那片黑暗。
屏幕再次静止。
安东跌坐回椅背。双手颤抖。口干舌燥。他明白了一切,又什么都不明白。
他明白了它们偷窃的不是物品。它们偷窃的是联系。钥匙–是与家的联系。手表–是与时间的联系。关于脸庞的记忆–是与过去的联系。旋律–是与情感的联系。它们从现实中将这些啃噬掉,留下空洞无意义的躯壳。
他明白了为什么她的饼干索然无味。它们吸干了其中一切可能温暖鲜活的东西,只留下被义务填满的形式。
他看着屏幕上裂隙库妮娅静止的图像。她是这片悄然蔓延的遗忘之海中一座孤岛。是它们的敌人。或是它们的目标。
他也明白了,现在他不能再只是观察。必须行动。不是作为梦想家,而是作为修复师。找到故障的源头。并修复它。
他关掉了笔记本电脑。公寓的寂静中,他自己的呼吸声显得过于响亮。窗外又开始下雪,缓慢而无动于衷,掩埋着窗台上的痕迹。但安东已然知道–有些痕迹并非通向外界,而是通向内部。通向深处。通向那些啃噬时间的生物爬出来的地方。
第四章 老鼠与票价
网络没有给出答案。搜索“窃取记忆的啮齿动物”和“发绿光的土拨鼠”,只出现关于痴呆症的心理学文章和粗制滥造的灵异视频。安东觉得自己像个疯子,狂热地翻找着一种不存在疾病的症状。
但他是个匠人。而匠人相信的不是言辞,而是肌理、痕迹、材质。事实如下:存在某些生物。存在一个被它们研究的玩偶。存在一个被它们夺走某些东西的他。战争已在他的领地宣告。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应战。
接下来的一夜,他没有睡。他不再用摄像头,而是布下了陷阱。不是捕鼠夹–他直觉那没用。他用缠绕了软布的台钳做了夹子,目的不是杀死,而是钳制。诱饵不是奶酪也不是花生酱。他在每个陷阱中心放了一小块……在衣柜里找到的旧教堂蜡烛的蜡。那或许凝结着某人无声而绝望的祈祷的蜡。希望。
一夜在紧张的等待中过去。黎明时分,他下楼到工作室,发现陷阱原封未动。蜡球完好无损,周围的灰尘上散落着细小、轻蔑的爪印。时啮兽绕开了它们。它们不以希望为食。吸引它们的,只有沮丧的苦涩、忧郁的酸楚。
绝望开始爬上喉咙。安东走到架子前,捧起裂隙库妮娅。瓷体冰冷,但并非刺骨。大拇指指腹再次触到了那块饼干屑的粗糙感。
“它们想要什么?”他低语。“又该如何把你和这一切联系起来?”
他在手中转动着她,目光落在那个紧握的小拳头上。以前他以为这只是个姿势。现在他仔细看去。在最纤细的瓷指之间,在拳头里,有一道微小、几乎看不见的缝隙。仿佛她曾握着什么,而那东西被强行取走,留下了虚空。
一个念头突然闪现,如同顿悟。不合逻辑,疯狂。既然它们窃取联系……也许,应该给它们提供某种东西,不是与忧郁相关,而是与她相关的?
他不知道她曾爱过什么。不知道她的故事。但他是修复师。他的职业就是恢复事物的完整性。他拿起最纤细的刻刀,一小块软蜡,屏住呼吸,小心翼翼地试图填补她拳头中的虚空。他塑形的不是具体物件,而是一个珍贵的、遗失的、重要的东西的概念。一滴水珠。花心。一粒种子。在他的手指间,蜡变成了一个微小、不完美的柑橘形状–这是他脑海中第一个冒出的东方审美意象。
完成后,他将她放回架子,放在那些蜡球旁边。然后开始等待。
夜幕降临,漆黑而繁星点点。安东没睡,潜伏在楼梯上。他看到熟悉的影子从踢脚板下爬出。它们和之前一样,无视了那些蜡制的“祈祷”。但当它们的头领靠近架子时,它停住了。它绿色的眼睛盯着的不是玩偶本身,而是她的手。盯着她拳中那个暗淡发光的蜡球。
它发出一声轻微的、尖细的声音,充满了贪婪和……认可。它跳起来试图够到,但架子太高了。于是它转身,朝其他同伴点点头,便溜回了踢脚板下。但并非全部。一只较小的留了下来。它坐在地上,盯着玩偶,像个守卫。
本能冲安东大喊:就现在!抓住它!但敏锐到极致的理智注意到了别的东西。这个啮兽守卫并非只是坐着。它那长长的、带鳞的尾巴拖在地上,尾尖微微颤动,敲击出轻微、有节奏的嗒嗒声。不是随机的。是有规律的。仿佛在……敲击密码。或者计算着路径。
安东尽可能悄无声息地溜下楼梯。他贴在墙边的阴影里,距离那生物十步远。他开始关注的不是那小家伙本身,而是它在灯串照射下投在墙上的影子。那影子长得不自然,而且活灵活现。它没有用尾巴敲击。它像一根纤细的罗盘指针,指向工作室远处那个角落–那里杂乱地堆放着油漆罐、旧墙纸卷,还有……一个红色的纸制中式灯笼,是玛莎阿姨以前买来“增加气氛”、后又因无用而被丢弃的。
安东深吸一口气。这是个信号。或者是个陷阱。
他向前迈了一步。啮兽守卫转过头,绿眼睛朝他闪了闪。但没有攻击。没有逃跑。只是继续坐着,而它的尾尖现在敲击的节奏,像是从容不迫的脚步声。
安东朝角落走去,远远绕开那只小家伙。那生物用目光跟随着他。他挪开桐油罐,拂去蛛网。灯笼挂在一颗钉子上,布满灰尘。纸张是红金两色,上面有个褪色的汉字“福”–幸福。
他取下灯笼。灯笼很轻,空荡荡的。但在他的手指触碰到纸张的瞬间,尾尖的敲击声停止了。安东转过身。地板上空空如也。啮兽消失了。
手中的灯笼突然变重了。安东朝里看去。在灰尘和死苍蝇中间,放着一小片仔细卷起的宣纸。他用颤抖的手指展开它。纸上用纤细、几乎褪色的墨汁画着一个简略的迷宫。下方有几个汉字,一个箭头指向其中一个出口。这是一张地图。或者说,一张通行证。
心脏狂跳。他将灯笼举到灯串旁。纸张很薄,光线透了过来。这时他看到–灯笼光投射在墙上,显现出的不是阴影,而是另一个图像。一扇门。一扇古老的木门,带有繁复的雕刻,隐约可见龙与凤的图案。一扇在他墙壁上从未存在过的门。
一阵吱嘎声响起。不是来自地板下。来自墙壁。安东难以置信地伸出手。他的手指触碰到的不是灰泥,而是粗糙、温暖的木材。他按了下去。门随着一声漫长、哀怨的呻吟向内打开。
门后不是邻家店铺的水泥隔墙,而是一个昏暗的空间,弥漫着焚香、旧纸张和……炒栗子的气味。一个狭长、低矮的房间,堆满了直至天花板的货架,上面摆满了各种杂物:破碎的花瓶、回形针、褪色的照片、缺了A的扑克牌、单只的手套。这是一个失落之物与未实现可能的垃圾场。
在深色木制的柜台后面,在一盏绿色灯罩的台灯下,坐着一只老鼠。
不是啮齿动物。不是时啮兽。是老鼠。体型如大猫,穿着一件磨损但干净的马甲,戴着一条金表链,上面挂着的不是放大镜,而是一个微型相机镜头。它长长的胡须颤动着,小小的黑眼睛看着安东,眼神里带着一种礼貌而疲倦的兴趣,就像一位被打断编目工作的老书商。
“进来,别磨蹭,”它用一种类似翻页声的嗓音吱吱说道。“门自己撑不住。性子收放自如。”
安东跨过门槛。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,融入了货架墙之中。
“我在哪里?”
“在中转站,”老鼠简单地回答,整了整马甲。“介于‘尚未’与‘已迟’之间。你可以叫我老鼠老。老耗子也行。我管理门户,交易……必需品。你带着地图来。说明你在找路。去找那个瓷姑娘,对吧?”
安东点点头,过于震惊而无法撒谎。
“她是位公主。她叫裂隙库妮娅。”
“知道,”老鼠老懒洋洋地挠了挠耳朵。“好名字。意思是‘缺失的一环’。或者‘命运中的缝隙’。看怎么翻译了。你想去找她?这可以安排。”
“怎么做?”安东脱口而出。
“需要票,”老鼠老拉出柜台抽屉,取出的不是车票,而是一个古老的骨质印章。“但钱在这里不通用。金子也不行。这里用别的货币支付。”
它用那双闪亮的珠子眼睛仔细打量着安东。
“你有些有价值的东西。记忆。尤其是温暖的记忆。特别是与技艺、手艺相关的。”
安东感到腹中一寒。
“什么……具体是什么?”
“让我看看,”老鼠老伸出爪子,并非触碰安东,而是在他头部周围的空气中摸索。“啊,有了。最珍贵的那个。父亲。工作台。刨子。第一片真正平整的刨花。那一刻,你明白了木头服从于你。技艺传承的时刻。非常优质的材料。纯净,没有怀疑的杂质。就拿它当报酬吧。”
“你想偷走我关于父亲的记忆?”安东的声音变了调。
“不是偷。是交换,”老鼠老纠正道。“公平交易。一段温暖的记忆–换一张通往某个领域的冰冷门票,在那里你很可能只会痛苦和恐惧。但她在那里。选择权在你。”
Конец ознакомительного фрагмента.
Текст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 ООО «Литрес».
Прочитайте эту книгу целиком, купив полную легальную версию на Литрес.
Безопасно оплатить книгу можно банковской картой Visa, MasterCard, Maestro, со счета мобильного телефона, с платежного терминала, в салоне МТС или Связной, через PayPal, WebMoney, Яндекс.Деньги, QIWI Кошелек, бонусными картами или другим удобным Вам способом.